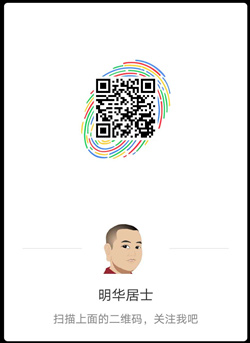相由心生 境随心转 刘素云老师主讲 (第六集)2010/4/9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档名:52-441-000
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各位同修,尊敬的各位大德,大家早上好!
今天上午这两个小时,应同修们的要求,讲一讲如何处理家庭关系问题。特别是重点讲一讲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夫妻之间怎麼样能达到和睦,达到美满。这个问题,我是作为一个反面教员,用我的切身经历讲给大家听。无论是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我讲别人讲不清楚,我就讲讲我和我老伴这四十四年是怎麼过来的,有哪些经验、有哪些教育,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说说我和我老伴婚姻的因缘。前几天,我曾经简要的说过,我和我老伴是初中同学、高中同学,他高中念了一年级就不念了,就上工厂去当工人。我老伴是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他的性格就属於争强好胜的那种类型。父母娇惯他娇惯到什麼程度?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我老伴比我大三岁,为什麼我俩最后能到一个班级去学习?因为他读书是倒著读的,怎麼个倒著法?从一年读到三年,三年读完了应该升四年,但是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怕这个宝贝儿子累坏了,怎麼办呢?不但没降一级,而是又回一年级重新读的。所以这样,前后不就差了三年吗?也可能就是这个因缘,使我俩成了同班同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要正常的读书,他肯定高我三个年级,那我俩就不是同学,不是同学,可能就没这段因缘了。也可能就是这麼安排的,就是这个缘分,就使我俩成了同班同学。
高一读完了以后,他进工厂当了工人。因为他的性格就争强好胜,什麼东西都得依自己的意见来办,你走上了工作岗位,走上了社会,不可能人人都依著你。你在家里,父母可以依著你,你到工作岗位以后,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他就遇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不知不觉的他就得病了,就得了精神病。是怎麼发现他得了这种病?一开始,那时候人们对这个不是太明白的,他非常爱运动,爱打篮球。我现在有时候跟老伴开玩笑,我说你真是一个人才,但是没得到发挥,我说你自然条件不行。我老伴说怎麼个不行?我说你爱打篮球,打篮球打得那麼好,投篮那麼准,满场飞,但是有一条,你不具备打篮球的条件。他说什麼条件?我说你腿短。我老伴现在经常不服气的说,有佛友上我家,他说你看我俩谁高?佛友当然就实事求是的说我刘大姐高。我老伴说,不对,你怎麼看的?我比你刘大姐高。实际现在真正的比起来,他确实没我高。但是我一直说,我老伴高、我老伴高,我说主要我显个,因为我腰板溜直,显个,我没有他高。你就得这麼说,来安慰他,就在这样的事情上,他都要跟你争个高低。所以这些年我已经养成这习惯,我什麼事也不跟他争。
他爱打篮球,就是在一场篮球比赛中,两个队,他这个队上半场赢了六分,那就是赢了三个球呗,我对这个运动一点也不内行。上半场赢了六分,三个球,下半场把六分输进去了,又输了二分,这不就又输了一个球吗?这整场比赛,他这个队就输了。当时他在篮球场就气抽风了,抽的大家都没法办,当时就给抬到医院去了。抬到医院,当时是一个老大夫,我记得个不太高,那老大夫有个特点,就是他手是又宽又短,大骨节,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好像大夫姓于,大概是。这老大夫就问送去的人说,他怎麼的了?谁也说不清楚,说他搁篮球场打完球,他就抽了。这老大夫就用手按他的人中,按也按不醒。后来,这老大夫也很有经验,就用语言来启发他说,你是不是有什麼委屈的事?你跟我说说,我能帮你忙。就这麼一说的时候,他哇一下就哭了,「我输二分!」他输二分。然后人家就问说他怎麼回事,输二分?送的人这回明白了,说打篮球,他带的那个队输了一个球,那不是二分吗?
就这麼的,从那以后逐渐逐渐精神病的状态就反应出来了。后来严重的时候,就得把家里玻璃窗的镜子,屋里照人的镜子,全都得拿牛皮纸糊上。因为不能见人,见人都是特务,就是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也是特务,他也不认识自己,就到这种严重程度。就是因为我老伴得了这种病,他的父亲看了他半年,老人家就高血压了。还有一个老母亲,身体状况也不是那麼太好,毕竟老人都年龄大了。这个时候怎麼办?所以我想,总得有人管他,不能像其他的精神病人在街上流浪,脏兮兮的,非常可怜。另外你想,两位老人就这麼一个宝贝儿子,如果这个儿子要是不行了,或者不存在了,两个老人肯定也就跟著走了,这整个家庭就没有了。所以我想我能帮他什麼我就帮他什麼。再说,我们同学在一起唠磕就说,素云,你最善良,你嫁给他,你侍候他吧。那我说我就嫁给他吧。
我就上他家跟两位老人说,我说我嫁给你儿子,我照顾他,你们两位老人不用伤心。当时两位老人都哭了,说孩子,我们不能看你跳火坑,这个病啥时候能治好,能怎麼样都不知道。我说没关系,我陪他。就这样,我结婚那年是二十一岁,要按照我家的条件,我在家是老姑娘,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疼爱我,我不可能那麼早结婚。但是为了照顾他,因为什麼?照顾他,你不结婚不方便。他尽钻高粱地、苞米地,钻到那个地里,庄稼一挡,看不著人,没有特务,安全。那你说,一个大姑娘,一个大小伙子,成天钻高粱地、苞米地,那怎麼办?没办法。所以二十一岁我就跟他结婚了。
结婚以后,我基本上是半天上班,那个时候我在小学当老师,然后半天陪著他。精神病人跑得特别快,不是说我领著他上哪他跟我上哪,而是他领著我往哪跑,我搁后面追著他往哪,就是这样的。有一次,看见一片麦子地,那个麦子是有点发黄了,但是没成熟。他就说,你看,这麼一大片麦子都成熟了,没有人来收割,雷锋都哪去了?咱俩做雷锋吧,咱俩帮著他收割麦子。我说不行,这个麦子没熟。他说熟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跟他强了,他说熟了,你就得说,对,熟了。那怎麼办呢?也没有刀,就拿两个手去薅麦子,给人家一片片的薅。薅完麦子说,好像是没熟,搁著吧。薅出来的麦子就给人放在那了。然后就上那高粱地,高粱地那个脑袋没窜出来之前,不是一个小包包嘛,我们北方人管那个叫乌米。我不知道咱们其他地区管那个叫什麼?还没窜穗。他就说这个东西最有营养,然后就掬下一大抱,抱著回家跟他妈说,这个东西最有营养,你赶快给它煮熟了,给素云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记得就这麼大一个小锅,烧灶坑,还得现架柈子、架煤,就是那种锅。然后老人不敢不做,就添上水,就把这个东西一扒一个乌米头,一扒一个乌米头,就这样,有的是穗穗,那不是还没窜出来吗。后来,煮好了以后,他妈妈说,这个东西不好吃,你让她吃了会把她药死的。他说,那能药死她呀?那不吃吧。就扔了。就到那种程度。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再想那些年是怎麼过来的,我自己都有点害怕。如果这个问题摆在现在,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



然后我和我老伴结婚,结婚那天,你说我在家老姑娘,这麼娇生惯养,爸爸妈妈那麼疼爱我,眼看著老姑娘嫁一个精神病,连人都不认,你说怎麼办?父母那种疼爱子女的心,我当时不完全理解,所以我就自己做主,就把自己嫁出去了。我结婚那天,从家出发是什麼样?我就一身衣服搁身上穿著,其他的我连个小包包我都没有。人家结婚都有什麼陪嫁,都拎几个包,我看还端个盆,盆里装著什麼东西,上面还盖著红布,我们北方都有这个习俗。我结婚那天,这些统统都没有,我就是空手一个人,身上穿著一身衣服。我连个换洗衣服都没有,我妈不让拿,都给我没收了,就因为不同意这门婚事。从我家走到我丈夫家,大约需要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我的几个好朋友送我去他家。从我家一出发,我们在前面走,我妈在后边跟著,一边哭一边骂,一直送到我丈夫家那趟房的房头才罢休,回去了。这是结婚那天。
结婚一个月,那可是真给我过满月去了。我妈妈来了,上我家来了,把门帘、窗帘全都撕掉,盆、碗、碟都摔了,摔的满屋都是碎碴子。当时我公公婆婆一声都不吱,两个老人坐在坑上,就瞅著我妈摔。还劝我:小云,别著急,老人心里有气,发泄发泄,摔就摔了,撕了就撕了!就这样,我妈就也骂够了,也撕完了,也摔完了,回去了。我丈夫在后面送我妈,一边送一边说,他管我妈叫大婶:「大婶!别生气,别生气。」就这样事的,给我妈送过房头。
我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我妈妈就这个时候是不允许我丈夫进我家家门的。我家姑娘三岁的时候,我老伴第一次能走进我娘家的家门。因为什麼?我妈不认这个女婿,不承认,所以不允许他上我家。我回家的时候,他帮我抱孩子,抱到我妈那个房头,把孩子递给我,他扭身就走了。后来我用什麼办法让我妈承认了这个女婿?我说妈,你看这个孩子可爱不可爱?我妈说,是挺招人喜欢的。我说你喜欢她,你就得喜欢她爸,没有她爸,怎麼能有她?就这麼一点一点渗透,最后我妈默许了。但是那话始终没说,说「我承认他了,他来吧」,这话我妈始终没说过。我就跟我丈夫说,我说现在我觉得差不多了,咱们试一试,你跟我一起进屋,你看看我妈有什麼表情?如果老太太还不允许,你扭头就走,别惹老人生气。老人要是不说啥了,你就大点脸,咱们就搁那赖著。就这样事的,我老伴第一次进我家门就是这麼进的。所以就这麼一个婚姻。我婆婆公公为什麼对我这麼好?他们始终把我看成是恩人,他们就觉得,这麼好一个孩子,嫁到我家太委屈了。所以老人,从我过门一直到老人去世,始终我们是在一起过的,关系都处得特别好。老人对我好,我就觉得我父亲、母亲对我,甚至都不如我公公、婆婆对我好,就是想得这麼周到。就是这样,所以我说人心比人心。
我和我老伴就是这麼个情况下结合的。我那个时候说实在的,不懂什麼爱情,完全是一种同情心、怜悯心,很简单的一种纯朴的善良的心,就觉得我照顾他,就是这样。后来结婚以后,他这个病是有多种反应的,他和正常人的思维不一样。他要说这个东西是怎麼回事,你就得说是怎麼回事。他要说鸡蛋是树上结的,你瞎话你就接吧,你说,对,那上还有把呢。你就得这样顺著他。你说按我在家里也二十来年养成的脾气,在家里都是爸爸、妈妈、姐姐都顺著我,你说我嫁出去以后,我就必须得顺从我丈夫,一开始特别不习惯,就想跟他争一个子午卯酉,谁对谁错。不行,争不了。
有一次我记得,我生老二是儿子,他抱著我儿子,我俩不知因为什麼,几句话就说崩了。说崩了以后,我眼看他就开始白眼珠往上翻。这不是他怀里还抱著儿子的吗?我一看大事不好,我一个手抓他,一个手抓儿子。你说他那麼大个砣,这儿子小一点我能提的动,他,我就提不动了。我就把儿子提到手,没摔著儿子;提了他,反正也减轻他摔的力,他就躺在地上。当时他穿著一个白色的短袖布衫,他这麼一躺的时候,就划一下就把,我家有个大鱼缸,上面有个小鱼缸,他就把那个小鱼缸划拉到地下去,整个都摔碎了,连鱼带水,带玻璃碴,满地都是,他一下子就躺在那上面了。他一抽的时候,他能颠挺老高,这个时候我就怕,别磕著他脑袋。我赶快把孩子放在一边,用我得两个手托著他的脑袋,那我就顾不了他的身子,他后背。这一颠一颠的,后来他整个小白布衫的后面全是血。因为啥?小鱼缸碎了,他在那上颠的,我只能护著他的头。
就是这样,从那以后我就想,他是这样一个人,你干嘛要跟他争对错高低,以后他全是对的。就是这样,但是心里不是很舒畅的。但是我知道,我跟他强,强不一个里表来,所以后来我逐渐就不跟他强去了。那个时候比较轻松在哪?孩子老人带,我就上班,他上班也经常出差,他是搞供销的,经常出去驻站。就是这样,见面的时候不是太多,他一年大约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外面的,这样矛盾就不太明显。后来矛盾就明显了,为什麼?我有病了,不上班,在家。他提前病退了,这样就每天都要面对,这个时候很多矛盾就突显出来。
这时候我的心里有几种呢?一是委屈,就觉得人的一生真是太不容易了,婚姻问题真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真是痛苦一生。另外,有怨气,就觉得我对你这麼好,你为什麼对我这样?我委屈到什麼程度?就是我一九九九年病重以后,二000年初,二月二十五号第一次住院。住院五十七天以后,不就出院了吗?人家医生说治不了我这个病,你不能打针、不能吃药,住院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出院了。出院了,我姑娘就是想带我去北京去看,这个时候我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我这次北京之行,我还能不能活著回来,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病特别严重。我就想让我老伴跟著一起去,我为什麼这麼想?因为我姑娘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她毕竟是个孩子。如果我出去了,我要是死在北京,你说让一个孩子她怎麼办?那吓也得把她吓坏了。这只是我心里的活动,我不能跟任何人说。
我就跟我老伴商量,我说,老伴,上北京去给我看病,咱们三个一起去呗。他说我不去。他不去。买票的时候,就买了两张票,我一张,我姑娘一张。我临出发那天,他送我上车站。我姑娘在车站跟她爸说,爸,你去看看卖票那里,现在这趟车还有没有闲票?要有余票,你再买一张,咱们一起上北京吧。我估计这个时候孩子心里也没底,但是她也不能说。我老伴去了,看了一圈回来了,告诉我,有票,我没买,我不去。还是不去,那没办法,就我姑娘我俩去了。这一路我心里真是很堵的慌,在我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真是希望丈夫能扶我一把,那怕我靠你肩膀,我靠一靠,我休息一会,我都觉得很幸福。但是这个危急关头,我老伴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个事对我刺激特别大,我特别伤心,但是我没有恨心,我就觉得挺伤心的。回来以后,就是那个时候,我那手都像鸡爪似的,伸不直,也攥不上。熬那中草药也挺麻烦的,你还得和,你还得看著火,往外炖那药汤。就这些工作,孩子们不在我跟前的时候,全都得我自己做,饭我得做,屋我得收拾。就是这样,所以觉得特别委屈。
然后我老伴又做了一些就是让人很难忍受的事情。我那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委屈到什麼程度。我那天我说了一句,我为什麼上普陀山抽了个签?这就是,如果那次我要不抽那个签,可能我真是,我就找个地方出家了。我当时想了这麼几条,第一条,出家,我眼不见,心不烦,我一心要出家。第二条,我曾经想过自杀。当时我家住的是七楼,我们家前面面临的那个街道,是我们哈尔滨比较繁华的街道,革新街,这一面就临著中山路。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是比较繁华的地区,我家住在七楼,两个屋和晾台都是面向阳的,都是朝南的。
有一天,谁都没在家,就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就站在晾台上往下望。我就想,我要现在从这个晾台上跳下去,一分钟之后,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不存在了,我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了,我也不会伤心了,我就这麼想。我为什麼没有跳下去?如果说按我的性格,我完全可以跳下去,我不怕死。尤其病到那种程度,又这麼很绝望的情况下,我为什麼没跳?我告诉你我想了什麼事:第一条,我一下子想到我家佛堂,我供的佛。如果我现在从这个地方跳下去,我家不可能一个人不来,人家来了以后,首先会发现你家是供佛的,就是念佛的人。供佛的人,怎麼还能跳楼自杀呢?你说人家看到我这个样子,谁还敢信佛?所以那个时候,说实在的,我要是自私一点,我不管,我一了百了,那我完全可以跳下去。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
第二个想到的,想到我学生。我从一九六四年参加工作当老师,小学、中学我都教过。那麼多学生,一听他刘老师跳楼自杀了,一是我学生接受不了,另外我学生可能饶不了我老伴,那会去找他拼命的,因为我知道我学生和我的感情多麼深。这是第二个想到的。第三个想到的,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单位工作,那可以说咱不会来事,那方面咱不会,但是工作绝对是认真的。在省政府工作,我是接触人少,但是据说前楼后楼的人家都认识我。因为什麼?因为我们大光荣板正对著四楼主楼梯的那面墙上挂著。我们那个光荣板上有大照片,我是大照片里最中间、最大的那个照片,而且是连著三年。所以不管是本楼的,还是外楼的,还是各地市来办事的,一上四楼,首先看到的是我们那个光荣板。这下子,那不得轰动了,全省都得轰动。人家说省政府谁谁谁跳楼自杀了,那可是有轰动效应。所以我就想,你是政府的,咱们不是大官,毕竟你还是个小官,一个政府的官员跳楼自杀了,怎麼解释?没法解释。
所以就前思后想,再想,我跳下去是什麼样一种景象?因为我们那是繁华街道,底下全都是门市,都是很高档的门市。我要是跳下去,我就掂量著,我能摔到什麼位置,然后我是一种什麼样景象。我们七楼是比较高的,那肯定是大概脑浆都得摔出来,鲜血淋漓更不用说了,那多惨!我自己死了无所谓,我不知道了,那时候我还以为我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呢。我就想,这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每当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心里犯不犯咯硬?是不是?人家曾经看见过,就这个地方,曾经楼上掉下来摔死一个人。你说我影响多少人?也可能这也是我的一念善心,就因为这几个理由,所以我没有跳下去。我就活过来了,活到了今天。
如果说我和我老伴那个时候的关系没处理好,我不认为是我自己哪做的不对,我都把它归罪於我老伴。所以这样,问题迟迟解决不了,我非常痛苦,我告诉你们,我们俩个曾经要离婚过,我那天中午跟大家闲唠嗑的时候,我说了一段。离婚是怎麼个程序我不知道,我老伴提出来,说咱俩离婚吧。我说,你要是想离就离吧,我说怎麼个离法?他说你起诉我,我不起诉你。我不知道起诉的概念,我说怎麼个起诉法?他说那你谘询谘询,你打听打听。我就打听我一个老同事,我打电话,我说大姐,明华要跟我离婚,我得上哪去办手续,怎麼个起诉法?我大姐说,你等著,我给你找个参谋。就是她的姑娘,她说你跟你刘姨说。我跟我大姐说我俩要离婚,我大姐一句劝的话都没有。后来我大姐说,离吧,早都该离了,我们都不忍心让你遭这个罪。就这样事的。
那孩子就告诉我,刘姨,你上十字街有个法院,上法院,进楼往哪边拐,上二楼,有个窗口,要一张表,填表,然后交给他。我就去了,这不就告诉我地方了,我就去了。去了,人家一个小窗口,一人男的搁那窗户里坐著。我说同志,我要表。他说你要什麼表?我说就是离婚那样的表,起诉那样的表。他就瞅著我说,谁离婚?我说我离婚。他就搁那窗口给我递出来一张表。我拿笔,我就站在那我就填。他说你那个笔不行,是油笔,你得用钢笔或碳素笔填。我说我拿家去填完,我再送来行不行?他说,可以。我就把这表拿回家了。
拿回家我就坐在佛堂那屋,就把这张表填了。填到那个离婚理由的时候,我就直截了当的填,性格不和,生活方式、方法不一样,这就是我的离婚理由。然后涉及到什麼财产分割,怎麼怎麼的,我就填我净身出户,啥都不要。这张表我就填完了。填完了,我说老伴,我给你念念,你看行不行?我就坐在他跟前,我就把这张表就给他念了。念完了以后,我老伴说行,挺好的,你送去吧。然后,我就把这张表下午我就送到法院去了。法院说得缴五十块钱,我就给人缴五十块钱。人家告诉我说这两天别出门,搁家等著传票。我说,传谁呀?人家说,谁离婚传谁!我说传一个不行麼,我老伴要离婚,你传他呗,你别传我。他说,两人离婚,必须得你俩都来。我说,那我就搁家等著吧。我回家我就告诉我老伴,我说这两天先别出去,等著传票,好去办手续。我老伴说行。我这个事就到此为止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有一天,突然的我农村的外县的一个弟弟,还有我市内的两个弟弟、弟妹,一起上我家来了。一开门,我还挺奇怪,我说你们开会了,怎麼一起来了?他们进屋坐下了,他们说,听说哥哥嫂子要离婚,我们来看看。我说谁告诉你们的?你们怎麼知道要离婚?我当时就想,一定是我老伴说出去的,他要不说,就我俩知道,这些弟弟妹妹怎麼都知道呢?后来我弟弟就问他哥,他说,哥,你是真要离还是假离?你要是真跟我嫂子离,我们支持,离婚以后,我嫂子的事归我们管,你的事和我们没关系。因为这些弟弟、弟妹都是我老伴这面的亲戚,就是我弟弟的父亲,和我公公是亲哥们,但是这些弟弟妹妹都对我特别好,就这麼说了,我老伴一声不吱。后来我那弟弟就给他叫到另外一个屋,就想单独跟他唠唠。我老伴不知道怎麼想的,就把弟妹也都招呼进去了。你说按正常人,是不是这事怕弟妹听,就跟弟弟说说呗。没有,他把弟妹叫进去了。
他们搁屋,我们在厅里。待了一会,进屋两个弟弟,待了一会我老弟出来了,气得小脸蜡白,没救了!没救了!就这样事的。我说你生啥气!你哥哥啥脾气,你还不知道?待会儿,把那个脾气最好的弟弟也气跑出来,无可救药!无可救药!他无可救药。完了就拽他媳妇:走,不管了,回家!他媳妇就拽他说,你看你干啥来了,你还没等劝好,你生气啥?就这样,就把那个弟弟又硬按住了。后来弟弟就问我老伴:你就告诉我们一句明白话,你到底离还是不离?你要离,你们该怎麼办手续怎麼办手续;你要是不离,明天我去把那个起诉书拿回来。我老伴就说了一句:按你的意见办吧。他没说他啥意见,跟弟弟说按你的意见办吧。我弟弟说:按我的意见办,就是把起诉书拿回来。就这样,这个事就这麼定了。第二天我弟弟就去拿这个起诉书,结果没有本人去不行,你必须得本人去签字,才给你退这个书。就这样,都闹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次,真是把我气到就是到一定程度了。我给我一个好朋友打电话,我说这个日子过不了了,我要离婚。我那个好朋友电话那边说:快点离!快点离!一天都别跟他过。就这样说的,说完了以后,我这好朋友问我,她说素云,我问你一句话,你一定要正面回答我。我说你问我什麼?她说如果你俩分手以后,明华有什麼事情,你能不能像路人一样不闻不问,我不管,和我没关系了。我说我做不到,如果他真遇到什麼难事,我要是知道了,我肯定会去管的。我这好朋友气的说:拉倒!拉倒!拉倒!离什麼婚,我就知道你不行;你那心那麼软,能狠下心来吗?拉倒!就这麼将就著过吧。
她就上我家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当时我气的我上我儿子家了,我搁我儿子家里面。我这好朋友上我儿子家说,素云,不行,我得给你送回去,我跟明华谈谈。我们就一起回我自己的家。一进屋,我老伴在家,我这好朋友和他也熟,劈啪给他一顿打,给我老伴揍了,我老伴也没生气。我好朋友说,你太不是个物了,你把我们素云都欺负到啥程度了,我得给我好朋友出出气。就这样,就这麼的,这两次闹离婚,都没离成。所以说没离成,对了还是错了?对了!离婚不行。你那个缘不了,你就离婚,你就行了了?了不了!现在和谐了,你说多好!由那样一种状况发展到这麼一种状况,天壤之别。我告诉你们怎麼变的。首先,我找我老伴的优点,我虽然不跟他叨咕,但是我默默的在找他的优点。第一条优点,这是我跟他不能比的,非常孝顺。无论是对他的爸爸妈妈,还是对我的爸爸妈妈,都那麼孝顺,就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他孝顺到什麼程度?我妈妈不是好几年都没让他进门吗?不认这个女婿吗?到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记得我和他一起去照顾我妈妈。为了让我爸爸晚上好好休息,因为老人家白天照顾一天太累了。我们家住的那是炕,就是有炕梢有炕头。当时我爸爸住在这一头,我挨著我爸,他挨著我,然后我妈在这面。为什麼这个顺序?他为了让我休息好,他挨著我妈,我妈一有动静,他马上起来。那时候我妈一天晚上,就说要尿尿得多少次?二十次都是少的。你说这个觉能睡吗?一说要尿尿,他赶快下地把尿盆拿上来,把我妈掫著坐在尿盆上,他在后面用身子靠著我妈,让我妈依靠著他。有时候一坐一个小时,她也不说她尿还是没尿,你还不能问。什麼时候我妈说尿完了,把我妈放下,把尿盆拿下去,有时候甚至一滴尿都没有。我妈到最后就有点像老年痴呆似的。就这样,所以这一宿,他就炕上炕下、炕上炕下,基本上叨弄这一宿,从来没有烦过。我说咱俩换换地方,你睡半宿,我来看我妈。他说不行,你明天上班,你累,你坚持不了。你说是不是个大孝子?就是这样照顾我妈,把我妈感动了。
就这麼多年,我妈虽然让他上我家了,但是不答理他,说话都带刺的,都没有好气跟他说话。就是这样,他把我妈伺候的,我妈感谢他了。怎麼感谢他的呢?我妈临去世的头一天晚上,那个嘴吧稍微都有点歪了,说话都不清楚了,就像外语似的,我都听不懂,我姐姐当翻译。我姐姐把耳朵贴在我妈嘴边,听我妈说什麼。我妈说了一句什麼?「小华是好人。」我丈夫叫刘明华,我妈说小华是好人。是不是对我丈夫的肯定!这是她在临终之前,可以说是最后的遗言。你说我听了以后我高不高兴?我老伴他高不高兴?他心里很安慰,老人家终於承认我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给他总结第一条,他非常孝顺。第二条,他很善良,他没有那些恶心、歹毒的心,真是很善良很善良。有些时候,他说话叫人不太好接受,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是怎麼想的,他有时候嘴说出来,他不一定能做出来。甚至你真是要跟他说说,这事你真想这麼做吗?他说,我也就说说而已。就是这样的。
再一个,他心应该说比较大量。比如说,因为他本身精神状态不是那麼太正常,他跟家里相处的时候,家里人理解他,但是到工作岗位,人家不一定理解他。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包括领导在内,人家不会那麼太理解他。从我结婚到他退休,基本上有七、八年他没有上班,没有工资,为什麼?领导把他打发回家,不给他安排工作,不给安排工作就没有工资。所以就这样,他在这个问题上,他能不去闹,和我有一定的关系。我一直劝他,我说靠我的工资,咱们可以生活,不要去找领导。就是这样,这些年就比较平静的过来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要是去找领导去闹去,那我也控制不了他。精神病人要是闹起来,那不是谁能控制他了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现在我就想,面对他目前的状况我特别安慰。他现在就是,我俩是一九九二年一起皈依的,一起念佛。他现在就告诉我,他说老伴,你不用为我著急,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能去。告诉我,你今生要是成佛了,你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是我助你成佛的。
所以现在我就给他总结第三条,我老伴是我的大善知识,他是阿弥陀佛派来的特使,他给我出那个难题,别人出不了。我要是花钱上道上雇几个人,说你们来给我出出题,考考试,不见得能出他这样的题,也不见得能请得来。你那时候想不通的时候,你就觉得怎麼出这麼难的题?真是让你难以过关。尤其是做为一个女人最难以承受的事情,就那样的关,我可知道那种痛苦是什麼滋味。但是现在我一关一关的过来了,我告诉你们过关的感觉是什麼?尤其是你最过不来那个关,你过了以后,你那个心情那个愉悦,用语言难以形容,那个轻松。过不来的时候真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注没注意,我这面耳朵下有一块斑,这面耳朵下面有一块斑,这就是那个红斑狼疮,这两块斑是怎麼起的?二00八年,一个亲情的关系,一个问题我没有处理好,我就陷进去了。陷进以后不能自拔,那个痛苦,形容形容就像什麼,就像一把双刃的利剑插在我心上,一会这麼搅和搅和,一会这麼搅和搅和,那个心疼。我真知道什麼最难放了,亲情!生死关我过的时候我没有这麼痛苦,我觉得比较轻松,我过来了。就这个亲情关,我二00八年遇到的这一关,我告诉你们,事先佛菩萨慈悲,提醒我了。
我昨天不举了两个例子吗,往生的例子,一个是张荣珍,一个是齐树杰,这两位大菩萨。就在我遇到的这个难关没有显现之前,他们两位大菩萨先后来提醒我来了,非常奇妙。有一天,早上我拜佛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谁要和我说什麼的,但是我又看不著。这个时候就是谁回来了?齐树杰,就是我昨天说的我们刁居士的丈夫。他回来跟我说了几段什麼话呢?他第一段话跟我说,他说按世俗的称呼我还叫你刘大姐,我是谁谁谁。把名都报了,这是第一段话。第二段话说,我确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身边,什麼品位,他的法号是什麼,就是那次告诉我的。第三段内容就是告诉我,他说大姐,你今年有一道难关特别难过,会让你非常痛苦的,可能你都会感觉到你过不去了,但是你一定能过去。大姐,你这一关过去以后,你就升了好大一个层次。这是齐树杰点化我的。然后隔了两天,就我第一个送往生的那个张荣珍,还是以这种形式,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告诉我,你有一道难关非常难以逾越,你这一关一定要过去。你说两个大菩萨回来来鼓励我、点化我,所以我特别感恩佛菩萨的慈悲,他们知道我多痛苦。不两天,问题出现了,完全应验了。
出现了以后,我实在是承受不了,一夜之间就起了这两块斑。起这斑是什麼感觉?晚上躺在床上,就像那青草发芽一样,你都觉得嗖嗖嗖嗖,就好像往外窜一样。第二天早上照镜子一看,两块斑起来了。红斑狼疮的特点就是对称图形,你要这边起一个,这边保证起一个,你要脸蛋这起一个,这旮保证也起一个,它全是对称的。就起来了,现在你看都快两年了,就掉到现在这种程度,多麼顽固。所以我说人哪不能生烦恼,你一次烦恼,就能让你痛苦好长好长时间。我说这个斑最好别掉了,你就搁这长著吧,对我是一个警示。我不太爱照镜子,但是偶尔的要照照镜子,我就知道,我这两块斑是怎麼来的,那我就不生烦恼,少生烦恼,它对我是一种警示,就是这样。
后来就是这一关,我真觉得过不去了,我跟就是跟我来的刁居士,因为我俩经常在一起绕佛。我说刁啊,我这一关实在是过不去了。我这人就是什麼事都公开、透明,我不隐瞒,我也没有说家丑不可外扬,我没有那种概念,我都跟她叨咕了。我说这一关我实在过不去了。小刁跟我说的什麼话?所以现在我都非常感恩她,是我身边的一个大护法、大善知识。她非常严肃的跟我说,刘大姐,那不行,这一关你怎麼你也得过,你过不去能行吗?我们还等著看你给我们做榜样。几句话说的我很震憾,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那麼多佛友看著我。二00三年这张光碟出了以后,我就成了名人,人家都看著我怎麼修,你怎麼能修成,我们好看你的样子。我一寻思,这一关我要过不去,我就堆绥了,我给人家做什麼样子,影响多少人呢?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一下子就好像振作起来了,不行,这关我一定得过。心一发,信心一坚定,这关我就过来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说我最近这七、八个月非常快乐,就是从那一关过了以后,到现在,我就真是法喜充满,成天乐乐呵呵的。
那个问题我就想各有各的因缘,无论是夫妻也好,儿女也好,各有各的缘,这一生一世凑在一个家庭,就是来了这个缘的。恶缘也好,善缘也好,你都要了,都要坦然去面对。我就琢磨老法师说那句话,说逆境是佛菩萨安排的,顺境也是佛菩萨安排的,既然你把自己交给阿弥陀佛了,一切都佛菩萨来安排。逆境、顺境都是财富,对人都是一种磨砺。我现在我才懂得那个词,叫历鍊,过去我不太明白,我通过这些具体事我才知道什麼叫历鍊。历练就是历事鍊心,你不经过这些具体的事,怎麼能鍊你这颗心?怎麼能知道你到一个什麼程度了?你有没有这个定力。如果你遇到一件事,你又生烦恼了,又发火了,是不是你定力还不够?你自己宽容心够不够?包容心够不够?你如果连你自己最亲的亲人,连你的丈夫你都不能宽容、不能包容,你能包容谁?能宽容谁?因为在家庭里,一个人反应是最最真实的,没有任何遮掩;你要对外人,你还可以装一装,包装包装,隐瞒隐瞒。你在家里面对你最亲的亲人,你一点隐瞒都没有,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你,那时候才能看你修行到什麼程度。这个问题我弄明白以后,我和我老伴的关系迅速扭转,我不是扭转他,而是扭转我。
我过去弄反了,我想,丈夫是天,妻子是地,我是跑到天顶上去了,我没把丈夫当作天。我虽然没有说我瞧不起我丈夫,我认为他无能,我没有这些想法,我也没有后悔说我嫁给他;但是总觉得这个家得我顶著,有时候我跟他发牢骚,我说老伴,你说这个家经济上得我顶著,精神上你们还得折磨著,我说这个双重压力,就我这单薄细伶的两个肩膀,真有点挑不动这个担子。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当你的观念一转变,也就是从学佛来说,你的念头一转变,一切法心想生,真是能改变环境。我就想从我自己做起,我怎麼样来面对我老伴我种种种种我看不惯的事情?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老伴非常乾净利索,他那衣服比我要洗得勤得多的多,连那线裤都白的。有一天他坐在椅子上,就把那线裤脱下来,我以为他要换裤子,脱下来以后,就从膝盖上面用剪子把两条腿就绞下来。我看了以后,我心里纳闷,好好一条线裤,怎麼把腿绞了?但是我没吱声。第二天,坐那旯又脱一条,又把两个腿绞下来了。我就看著你想干什麼呢?这回绞下来以后,把绞下裤腿那部份,人家就搁在地下,拿脚踩著人家擦地。这时候我就问了一句,我说老伴,那不是有擦地抹布吗?你怎麼把线裤绞了擦地?他说因为我这线裤乾净,它擦地就乾净。你说你是批评他,还是指责他?既然是这样,那就擦吧。要搁过去,我肯定就跟他激了,你这不是败家吗,造害人吗?你说好好的裤子就把腿绞掉,就擦地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要不转变心态,我肯定跟他干仗。
比如说去年他病了,他要看病,我跟他商量。我说老伴,你可想好,你去不去看,这是第一;第二,你看了以后拿不拿药,这是第二:第三,你拿回来的药,你吃不吃,打不打。你把这三条想好了,你再去做。他说我看病。就把姑娘、儿子都找回来,领他去看病,看病说脑梗,就给他开的药。我这人心眼实,我一次出去把所有药都给买回来,连口服的、带点滴,好像一次就一千多块钱的药,我就给买回来了,买回去打点滴,应该是十五天一个疗程。打了大概是六、七天的时候,将近一半,早上吃饭时跟我说,老伴,你告诉那大夫别来给我打点滴,我不打了。我以为他开玩笑,我说还有一半,打完了再说呗!我说打完了再去看看。他说,不打了,你告诉他。我看他叫真了,我有点急了,我说你干嘛,我事先跟你说,你自己决定看不看、拿不拿药,拿药你用不用,你自己也决定的,你怎麼现在又秃噜了?我跟他说的时候,我态度是不好,因为急了。我这态度一不好,什麼样的结局?因为我刚把饭菜端上来,摆在桌上。我老伴就这麼「哗」家一划拉,杯、盘、碗全都划地下去了。那就整个厅,就佛堂门口都喷上了,你说连汤带菜的,就划拉到那种程度。有的盘子掉地下它没打,他看那没打的盘子,他去捡再重新摔,把那没打的盘子再摔碎它,把地板就磕了好几个坑,就这样事。要搁以前,那我就得跟他真是不打仗也差不多!这一次我生气了,但是我没跟他吵。我楼上的那个弟妹下来说,这怎麼整的这种程度。我弟妹收拾的,我说你不用收拾,实在不行就搁著、摆著吧。
比如说,我老伴心里有两个不平衡,一个不平衡就是职务,第二个不平衡是工资。他就跟上我家的人说,就说我,上学的时候她啥不是,我是班长,现在她跑省政府当处长去了,我啥不是。一开始我以为开玩笑,我还说,我说老伴,不管我在工作单位是什麼长,我回家不是你老伴吗?我还这麼给他解释。后来我发现他是认真的,他真是不平衡了。所以我一九九七年才把这个处长辞掉的。我为什麼自己提出来要把处长辞掉?我就是为了让我老伴心理平衡。我辞掉了以后,我也是老百姓了,咱俩就划等号了。我老伴后来说,那等还不是等号。我说那怎麼的?他说约等号。我说约等号也差不多了,咱把它一抻不就直了吗?就这样事的。就是这麼地,这是我其中把处长辞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让我老伴心态平衡,这是第一。
第二,工资。工资,我老伴工资肯定没有我高,他在企业,我在机关,现在这个差距是很大的。他心态不平衡,就觉得我没面子。尤其有些人上我家里,还好问你挣多少钱?我就怕他们提这个碴儿,因为提这个碴儿,我老伴一听他心里就不痛快。后来我姑娘给想个办法,就是家里的所有的用都不用他爸操心,他爸的工资就是他爸的零花钱。所以从一九九七年到现在,我老伴的工资啥样我没看见过,家里不花他的钱。如果我有时候实在没钱了,我管我老伴借,借完了,我有钱我再还他。我就想,不要让他心里不平衡,他工资比我低,他已经不平衡了,如果我再抠他那点钱干嘛呀?所以现在这两个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
过去我老伴可有意思了,他要出去上市场,或者碰著了,买了两根黄瓜。一进屋就举著这两根黄瓜:报销!报销!我就得赶快给他报销。人家把黄瓜买回来就不错了,我就赶快给人家钱,还得多给。我要管我老伴借钱,我说老伴,借点钱,到时候我还你的时候我给你长利息。这高兴,他知道我说话算数,所以把钱愿意借给我。借给我以后,我有钱了我真是多给他,实际也就是让他高兴呗,你说不是一家人吗?,他们说我放权放得彻底,我说就彻底放,我就属於不会管钱、不会管事、不会管人的那个类型,我的大脑是空白的。这麼多年,因为我老伴是这种状况,就把我硬推到第一线上去了,否则的话,我啥事我也不管。我开了工资往家一缴,摺给你们,你们愿意怎麼办就怎麼办。我就是三条:有念佛的地方,有吃饭地方,有睡觉地方,就足够了。现在这不都有吗,就行了,我非常容易满足。捡谁家的衣服,我都能穿个十年二十年的,我穿衣服还省,我还不挑,你说这多好!所以,现在我和我老伴的关系转变,我总结的经验就是,从自己做起。我心态转变以后,第一个感觉,我看我老伴不别扭了。过去他一说话我就别扭,我一瞅他我也别扭,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我就觉得我老伴我瞅他很可爱了。真是这样,你说在不在自己的心态?我这面一改变,他那面马上就跟上了,灵!我告诉你们,我不骗你们,真灵。我不去跟他说什麼,我这面我就做,他那面他就在改。现在我告诉你们,我才知道家庭和谐是什麼样,我现在我和我老伴应该是说和谐的,但是是不是和谐到那种尽善尽美的程度?还不是,有时候还可能还有意见、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我就采取三条,不争论,不讨论,不辩论。如果对一件事认识不一样,放下,把那个我执放下,你别老认为我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他也不认为他如何,我俩现在这点非常统一,遇到认识不一样的问题,问题放下,不立马去解决,非得要说谁对谁错。过些日子,自然而然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也不用争论,也不用辩论,也不用讨论,大家都心平气和,谁也不生烦恼。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学佛的人,就在家里、在外头,你看看你有没有凝聚力,有没有亲和力。咱们就像一块磁铁似的,如果能把你周围的人都吸引到你身边来,他们愿意和你接近,那说明咱学佛还做的可以。如果人家都远离你、都讨厌你,不愿意亲近你,那说明咱们学佛有问题。所以我就每天我都检查我自己,我今天遇到的这些个人,到我家来的也好,还是我出去接触的也好,我有没有贡高我慢?我这人比较随和,要不他们为什麼都比较愿意接触我?我贡高我慢比较少,我不会,我不会贡高我慢,我觉得我没啥可贡高我慢的。你说得了这场病是没死,活到现在,又活得挺健康,就够意思了,你还有什麼贡高我慢的。我就想,大家凑在一起也是缘分,和和气气的,你把家庭问题解决好了,人家多少人在看著你。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有多大的力量,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我都没有想到。就是我来的头十来天,平房的一些佛友来看我,好几个都是我那时候的同事,就是都是老师。我老伴和他们不熟悉,有的甚至他都不认识。我们在一起唠嗑的时候,我真是没有想到,我老伴就来了一通发露忏悔,特别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大家都愣住了。他就把他最见不得人那个隐私,自个全抖落出来了。我听了以后我都莫名其妙,因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那些同事,就去的那些佛友,对我老伴是一阵赞叹,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当时人都说,这才叫大菩萨,人这真是表法。一般这事,他自己要不说谁知道,有的事我都不知道,人家那天就当著我这些老同事的面,人家就说了。
说了以后,你们知道起多大作用吗?过了两三天,来的其中一个老师,曾经教过我姑娘,曾经教过我儿子,来了一个电话。我一接电话,她说刘老师,我可得跟你报告报告。我说你报告啥呀?她说你们家那位大菩萨这一顿忏悔,你知道起多大作用吗?我说我不知道,反正那天他说,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麼一番话。她说他的一顿忏悔,把我家忏和谐了。我就特别纳闷,我说怎麼就把你家忏和谐了?。她说我就一对照,我和他说的,我和你一对照,我一想,我嫁给我老伴以后,这一辈子我都觉得憋屈、委屈,我怎麼嫁给他了?你都不知我这几十年是怎麼过来的。她说我在你家一看,你们家大菩萨一忏悔,一对照你的言行,我太惭愧了。她说我回来,非常迅速,立马对我老伴的态度就改变了,我家就和谐了。她说我家这两天可和谐了、可好了。我听了以后我也挺开心,你想想,一个人就这麼一番话,能让另一个家庭和谐了,了不得。咱们学佛,一定要学到真地方。所以我非常赞叹我老伴。
这次我来香港,极其支持,要搁以往,他可能得阻拦阻拦,这一次是一点也没有阻拦,而且极力支持我。你去吧,你不用掂记我。因为我老伴年前,他不是脑梗吗?打了半个月的点滴,吃了将近一个月的药。所以现在我这次出来,我跟他说,老伴,这次我出去,对你我多少有点不放心,有我在你跟前,你要有个啥事,我就能及时处理。他说,老伴,你出去,没关系,还有阿弥陀佛管我,你出去以后,我就接著念阿弥陀佛。这个他能做到,他是骑自行车,他告诉我,就这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是骑自行车绕,出去绕去,念阿弥陀佛。我是走步绕佛,两步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我说,当我自己改变了以后,我就觉得整个家庭的气氛都改变了,自己都有明显的感觉。佛友们上我家都说,一进你家,就觉得特别清净,清凉凉的,就搁这一坐,可舒服了。真是这样。你说一个家庭和谐了多好。一个家庭,夫妻和不和谐是主要关键,夫妻和谐不和谐,女方起很大作用。首先,你对丈夫,你是不是把他当天来对待?现在都实行女强人,我不太赞成这个词。我主张女人还得像刘善人说的,应该像水一样,别整的像钢一样。女强人这个词,我不知道谁发明的,什麼时候时兴起来的,反正我不喜欢做女强人。咱们在家,还是应该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这才是我们女人的本分。老法师不再三讲那三太吗?过去咱不知道,我要是没结婚前,我就知道这三太,我估计我一定是个好的妻子,好的母亲,我会向三太学习的。现在知道有点晚了,但是现在学也不晚,咱过去没做到的,咱现在一点一点来做。
另外,就是咱们对对方有没有控制和占有的念头?说白了,总想管著对方;不要管,管不了。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尽弄笑话,我可能出洋相了。有一次,一个佛友到我家跟我说,刘姨,我有个难题。我说你啥难题,你跟我叨咕叨咕。她说我丈夫,我嫁给他以后现在是十八年了,我嫁给他的时候,我是姑娘嫁给他的。他的前妻在他儿子一岁的时候跟别的男人跑了,就把她的丈夫和儿子扔下不管了,我可怜他们父子俩,我就去帮他干活,收拾家。可能后来就有感情,她就嫁给他了。这样不就又组成了一个新的三口之家吗?她为了照顾这个孩子,她没有自己要孩子,一直把这个孩子养到十八岁,她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她儿子已经十八岁。她说儿子和我感情特别好。她说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我说什麼难题?她说,他前妻回来管我要丈夫、要儿子,我想不通,我不想还给她。她说刘姨,你说我这个事怎麼办?我说你要问我怎麼办,我给你解释解释。我说,丈夫,什麼叫丈夫?她说丈夫就是老公呗。我说那是现代的说法,我的解释是传统的。我就连比划带给人解释,我说,丈,是表示距离的,一丈远;夫,是你的夫君。合起来就是一丈之内是你的夫君,是你的老公;一丈之外,愿意是谁的是谁的。
时有佛友在场,都说你这解释太新奇了,从来没有听说。既然是这麼的,那怎麼办?还给她!我说你要听我劝,还给她,你把丈夫和儿子都完好的还给他的前妻了,他们又是一个三口之家。她说那我呢?我说你清净念佛,是不是?两全其美!这面一个新的完整家庭,本来人家就是三口之家。我说不是你破坏她家庭,而是你帮著把她丈夫侍候到现在,把她儿子养到十八岁,你有功德,你再把他还给她。我说现在你要打起来,你不还,你啥功德都没有了,你连福德都没有。她听听说,刘姨,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是做起来真是难,他现在是我的丈夫。我说那就看你丈夫的选择了,人家丈夫愿意回去,儿子也要认亲生母亲,你就还给人家,成全人家,你就是自己有点委屈,你也认、也受,就完了呗。后来她说,刘姨,你给我解释完了,我心里就像亮堂了似的。
我说供你参考,要叫我,反正我就这麼处理。你要是我想控制你,我想占有你,我死死的把你拢在家里,我不让你和对方接触,我说人那个腿是长在他身上,你能看住吗?现在通讯工具这麼现代化,你能看得住吗?你累不累呀?如果你把精力用在看你丈夫,看你儿子,不让他们三口碰头,你成天就琢磨这个事,你啥时候念佛?你还有心思念佛吗?你今生能成就吗?你哪个事大、哪个事小?他也巧,过一段时间我听老法师的学佛问答,就说了这麼个问题。说什麼问题?就说有一个佛友,向老法师提问一个问题,就问老法师,说她有个佛友的丈夫在外面包了个二奶,她这个佛友心里很不痛快,请问老法师这个事怎麼办?我记得老法师是哈哈一笑,说难得你清净念佛!那我理解就是人家外面包个二奶,有人侍候他了,代替你了,你这面老老实实清净念佛,多好,什麼事也不麻烦你了。我一听,给我高兴的哈哈笑了,我想我给解释那丈夫解释对了,对不对?你说你一丈之内你都控制不住他,一丈之外你能控制住吗?乾脆,放下吧,别控制了,太简单了。
为什麼我敢这麼说?因为我都经历了,是不是?我要没有不经历,我这麼说你们可能不服气,你尽说大话,你没碰著,碰著你能想得通吗?我想不通过,我痛苦过,我哭过。我那时候每天早上我起来拜佛四个小时,磕四个小时头,我能哭四个小时。我告诉你们后来我怎麼通了?佛菩萨点化,要我说我福报大,佛菩萨对我特别关爱。有一次,我到省图书馆那院里去绕佛,从我家走到省图书馆大约得需要十分钟。我那个时候是早上三点钟起床出去绕佛,那不是外面还是黑的吗?我在这一路走的时候,反正也没人看著我,我就痛哭流涕,委屈的不得了。就这个时候,就四句话告诉我了,说:「娇儿莫哭,好好修行,带儿回家,父接儿行。」我就好像满天的乌云一下都散掉了。谁是我的父亲?阿弥陀佛!我就是阿弥陀佛的娇儿。现在父亲看我是委屈,所以马上告诉我「娇儿莫哭」,我就像那小娇孩似的,告诉我好好修行,「带儿回家」,就等到你回家的时候,「父接儿行」,父亲来接你。你说你还有啥想不通的?一下子烟消云散,我就快乐了。
我不是有什麼本事,我有多大能力,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念佛的老太太。我真知道佛菩萨是怎麼加持我的,是怎麼点化我的,我不敢多说,我说多了我怕引起误会,怕误导大家。心说,她怎麼都知道呢?佛菩萨怎麼点化她,不点化我呢?我就告诉你,心清净,你心清净了,佛菩萨就点化你了。当你真是老老实实念佛,你一心要回家,你那种真诚心发出来的时候,实际佛菩萨时时刻刻没离你的身边,你只是看不到而已。我真是这种感觉,你们如果心清净了,念佛念到一定程度,真是发大心发大愿,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的。
下面我再想跟大家说,家庭关系处理好,还有一个可能家家都能遇到的问题:夫妻俩双方的亲戚。很多是因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发生矛盾。比如说我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我公公家的亲戚多,我婆婆家的亲戚也多。老俩口往往因为这个事情有矛盾,就是你家的亲戚来,优待了,我家亲戚来,慢待了,老俩口有这方面的矛盾。我结婚以后,我看在眼里,乾脆这个事两位老人谁也别操心,都我来管。所以不管是公公家的亲戚来,还是婆婆家的亲戚来,我都一视同仁。我告诉你们,反正他们来全都是,不是要钱就是要东西,全是穷亲戚。昨天胡老师不是说,你穷亲戚上你家门来,你是有福,你有福报,你别瞧不起人家。那时候我家也不富足,我那时候工资你看二十九,三年以后涨到三十二,又过了三年涨到三十八,然后就十几年就三十八,一直不涨工资。我老伴因为精神状态不好,时不常领导还给打发回家来,打发回家就没有工资了。我公公那时候工资好像是五十八块五,就这样支撑这个家。但是亲戚朋友两方老人的亲戚来,我都全力以赴,我该给拿啥拿啥,实在是没有了,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那个老姑婆来了,因为我公公他们家哥们多,女孩就我老姑一个,那也是娇生惯养的。叼个大烟袋,可厉害了,三句话不来拿烟袋刨你。就这麼个老姑婆,对我特别好。来了以后,就想跟我说点什麼事。我婆婆就拽著我:小云,你过来,我先跟你说。老姑拽著我:小云,你过来,上你屋,我先跟你说。两老太太一家拽我一个胳膊,都要先跟我说。我就跟我婆婆商量,我说我老姑是来的客人,先让我老姑说吧,一会儿说完了,我再上这屋,您再跟我说,行不行?我婆婆那嘴一撇,不愿意了,「那你先说」。就这样事的。我就跟我老姑上我那个,我住那小屋小,也就六米吧。我说,关上门,老姑,您要跟我说什麼?小云,这次来我找你有事。我说有啥事?给我弄一百块钱。我说干嘛弄一百块钱?那个老三要定对象,农村管那叫过彩礼,「过彩礼,你得给我弄一百块钱」。我说,老姑,我刚开完工资,加上攒的钱,一共有五十六块钱,我都给您拿去行不行?「那不行,不够一百,你出去给我借点。」让我出去给借点。我说老姑,您侄儿出差新给我买回一套衣服,拿衣服顶,行不行?我老姑说:拿来我看看,什麼衣服?。我就把我那个小箱子拿来,就打开了,两个箱子我都给打开了。我说老姑,您自己随便挑。因为我就那麼一套新的,我老伴出差新给我买回来,我记得淡苹果绿色的,套服,裙子,上面是那样的,挺漂亮的,我一次没穿过。我穿新衣服我出不了门,所以我这新衣服就搁这箱子里放著。我老姑一下就相中,「这套行」,从箱子里就提了出去。我婆婆从那屋两步就窜到我跟前,就给摁住了:那不行、那不行,我们小云就这一套新衣服,凭啥你给拿去。这个老太太就往那边抢,我婆婆就摁著不让给拿。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我老姑相中,她就拿去吧。这套衣服据你侄儿说,好像是四五十块钱一套,我说加钱凑起来够一百,行不行?我说多少就这麼多了。我老姑说,这行,五十六块钱也给我拿著,这衣服我也拿著。就是这样。这一次我可把我婆婆惹生气了。等我老姑走了以后,我婆婆这下跟我翻脸,说你怎麼回事,就那麼一套新衣服,你还给她拿。就这样的事。
我婆婆和我老姑这两个老太太,这不是嫂子、小姑子关系吗?年轻时候就不和,那都是打著过来的,谁也不让份。来我家都到什麼程度,有一天半夜,我听两老太太吵起来了。我赶快跟我老伴说,两老太太吵起来了,快点过去看看。我俩就起来了,起来到那屋,什麼景象?两人都那麼大长烟袋,一个脸朝南,大烟袋这样抽著;那个脸朝北,背靠背,大烟袋抽著。我说干啥,两个老太太,怎麼半夜三更吵起来了,什麼问题没谈拢?我说,有问题,咱们明天白天商量行不行?晚上睡觉。就这样,你就像哄小孩一样哄著她。
所以我家就是公公和婆婆在这方面对我就没什麼挑的,她觉得我心好。我虽然有时候说话比较冲,我脾气比较强,但是我确实是我比较心眼好使,所以哪面亲戚来都行。我老伴上农村串门,告诉我那个弟弟,我那弟弟说需要钱,我老伴就说,上我家去,你嫂子手里有二千块钱,你管你嫂子要去。我这弟弟就来了。我那天给大家说了一次,我这两千块钱是我病重的时候,我们一个市的经委主任,一个女的,我去的时候我俩经常接触。她知道我有病以后,她就说刘大姐病那麼重,我没有时间过去看,托出差那个老处长把这二千块钱带给我。老处长回来,我就给人说了,我说你怎麼拿回来你就怎麼送回去,这不行。我们处长说,我当时我就说了,我不敢拿,拿回去得挨说。后来,老处长老伴老大嫂说:素云,你看你就这样让你大哥再给送回去?我一看挺为难,我说那样吧,先放著,等我病好了我自己来处理。我老伴不就知道我手里有二千块钱吗?上农村串门跟那弟弟说,你嫂子手里有二千块钱,你去要去吧。我弟弟就来了,说嫂子,听说你手里有二千块钱。我说是。他说我需要。我说你需要你先拿去吧!我就把这二千块钱给我这弟弟拿了。
过两天,又一个叔叔家的弟弟来,嫂子,我也需要钱。我说你需要多少?我需要三千。我二千我都给出去了,我没有三千了。那时候工资摺在我手,我说赶快拿工资摺看看,有多少钱?一看有一千六百块钱。我说弟弟,我这上就一千六百块钱。我弟弟说,嫂子,不够,你再给我凑凑。这时候我就跟我老伴商量,我说老伴,你再给我凑一千四。你把你工资摺拿出你看有多少钱?这样就凑足三千了。我老伴把他工资摺拿看看,他有多少钱最后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只能给他凑四百。我一想,我这一千六,他凑四百,这不就二千吗?好歹是抠著出来四百。我说:行行行,你给凑四百,二千。我说弟弟,先拿二千,以后需要再说吧。就这样,上那个叫储蓄所还啥地方,就把我这钱也取出来,我老伴四百也取出来,给我这弟弟又凑了二千。
过了几天,我那老弟弟,叔叔家老弟弟来了:嫂子,我需要钱。那时候我还出不了门,我刚搬到现在住的这地方。我说你需要啥钱?他说我买了三亩地还是多少地,我对那个不会计算。他说我需要雇人翻,怎麼的,一样一样给我算,我需要钱。我说你需要多少?我需要一千五。我说你需要一千五,我这真没了。没了,我说怎麼办?我就打电话,给他借钱。我说你坐著等著,别著急,我给你借。我就打电话,打给我姑娘的原来一个同事。我说:桂芹,你手里有没有钱?她说有,刘姐,你要多少?我说一千五。她说你等著,一会儿我给你送去。这不是挺痛快的吗?我挺高兴的,一把我就把钱给借著了。我当时心里挺痛快,我要借不著我出不去,我上哪给他借?新搬的这房子。
桂芹马上就问了我一句:刘姐,你要钱干啥?我不会撒谎,我说我老弟来了,他需要。一句话说坏了,那面就说:刘姐,我没钱、我没钱。我说你刚才不是说有钱吗?怎麼这麼一会儿就没钱了?她说他来借我没钱,那是骗子,他都骗你多少把了,你怎麼还上当?我说,我求求你,桂芹,就算他骗我了,他现在来了,他就在我跟前坐著呢。桂芹说,不行,我不管他坐不坐,我没有。她就说她爱人出差了,就给我扔二百块钱零花钱。我说那桂芹实在不行,你把你那二百块钱也给我送来吧。我都到这种程度了。桂芹说不行,二百块钱我还留著零花。不给我送了,我这又傻眼了。我就说我那弟弟,我说瞅你这臭人缘,你说刚才借钱有钱,一说你,人家没钱了。我说再想办法吧。
我就给楼上那老弟弟打电话,我知道我老弟弟没有钱,他搞汽车修配,他在一个工厂。我就打电话,我说老弟,给嫂子弄一千五百块钱。你问问你们单位会计,有没有现金?先给我借出来,马上送回来。我老弟就去问去了,回来告诉我,嫂子,有现金,我一会给你送回去。问我,嫂子,你要那钱干啥?我倒吸取教训,别说实话,我又说实话了,我说谁谁谁来借钱。我老弟当时我估计要在我跟前,那肯定是眼珠子都瞪圆了:不行,嫂子,谁都能骗你,你东郭先生啊!没钱,没有了。我说,求求老弟,你快点给我送来吧,太著急了。后来我老弟说,嫂子,怎麼办呢?我要不给你送,我怕你著急上火,你又出不去门;我给你送,我真不甘心。他说那样吧,我给你送一千。我就让我这个弟弟说,你谁给我送回来?他说我派谁谁谁。
派回来给我送钱的这个男孩,管我叫二娘,来借钱的这个就是他的亲叔叔,就这麼个关系,就拿这一千块钱来给我送回来。送回来这就快到中午了,我又做中午饭。吃完中午饭,我就告诉送钱这个孩子,我说你把你老叔一定要送到汽车上,汽车关门已经开了,你再上班去。我为啥这样安排?我怕他不坐车回家,他把这一千块钱再败光了,那不又没了吗?我就派这人看著他的。结果这孩子听明白了说:娘,行,我把我老叔送上车。吃完了饭,把他老叔送上车,回头打电话说:娘,我把我老叔送上车了,车开走了我才上班的。我说那好。
这时候我就心里琢磨,是真的是假的呢?我先给我大弟弟打个电话,就是我这个老弟弟的亲哥哥,这个弟弟办事把握。因为他说了几条理由,他说他哥给他拿了四千,这是一条。我就打电话给我这大弟弟,一打电话我就问了,我说你最近是给老弟拿了四千块钱吗?我这大弟弟一听说:嫂子,你肯定又上当受骗了,没这事,这四千块钱这事没有。我说老弟买了三亩地吗?没有!我说他是开摩托车把人家一个老太太撞伤了,人家让他包钱吗?因为这都是我老弟跟我说的借钱的理由。我那个大弟弟说没有。三条,一条都没有。他说嫂子,你别著急,我今天我就去把这一千块钱给你追回来。我说拉倒,既然我给他拿过去了,我就没有想往回要的想法。我说拿去就拿去,你也别跟他惹气了,我说我知道真实情况就完了。我这个大弟弟特别认真,第二天早晨起个大早跑到老弟家,去给我追这一千块钱。结果到那,这一千块钱花没了,就一夜之间,花没了。给我大弟弟气的,来电话说:嫂子,就这一宿,人家钱已经用了。我说你看,不让你去,你怎麼非去,用了就用了呗,你看你这麼一去。他说我把他们俩口子都骂了,我说你们有没有人心,咱嫂子病到那种程度了,连门都出不了,你还去骗她,以后你怎麼去见嫂子。一顿臭骂。
从那开始到现在,我这个老弟弟不敢登我家门。上次我大弟弟去世的时候,我见著我老弟了。我说老弟,过去事就过去了,如果你正而八经过日子,你有困难了,你去找嫂子,嫂子肯定会帮你的。我说你成天吃喝嫖赌,嫂子没有那麼大能力供你,我也不支持你这个,你夫妻俩都赌钱、赌牌,那是无底洞。我说你得好好过日子才行,你真是过日子遇到难题了,嫂子肯定会帮你的。他说,行行行。就是到现在,他都不好意上我家来,那不能再骗了。
再说,我这不是那个弟弟二千拿去了,是我老伴告诉的,那个弟弟来拿了二千。过些日子,就是过了大约一年多时间,我有一个弟弟就给我还回来一千块钱,我弟妹来了。来了以后,我说你干嘛来了?她说嫂子,我来还钱。我就赶快把她拽到我那屋。我说你还什麼钱?她说嫂子,不是搁你这拿了二千块钱吗?老太太过生日,大家随份子,我收回一点钱,我先还给你一千。我说拉倒拉倒,你那麼困难,你还我干啥,你拿回去吧。我说千万别,这回我真搞小动作了,我说千万别让你哥听著,让你哥听著肯定把这一千块钱扣下,你那还挺困难的。我这弟妹说:嫂子,那行吗?我说:行,这个事你就听我的。我俩出来,我俩是搁屋里嘀咕的,真搞小动作了,为了瞒著我老伴。等我俩出来,我老伴就问:你干啥来了?我弟妹就说,我来看看我嫂子。我老伴就那样眼神瞅她:你也不是好串门的人,你怎麼来看你嫂子?就这个意思吧,但这事就过去了。
回去以后,我这弟妹肯定跟我弟弟说,结果我这几个弟弟凑在一起唠嗑,就把这话唠出来了。我老伴去串门,一下子就知道这个事了。这下回家跟我作的,回家就问我,一进屋,我一看脸就不对劲,我想糟了,肯定有啥事。我也不敢问,我老伴就说:你有什麼事瞒著我?我一听赶快坦白,我说:是不是那个一千块钱的事?你还知道一千块钱的事,怎麼回事?就审我。我说:慕玲来是还一千块钱,我寻思她家挺困难的,我让她拿回去了。「就这事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敢做主?」我说那钱不是我的钱吗?我就拿这理由跟人掰扯,我说那不是我的钱吗?我愿意给她我就给她,也不影响你。这更生气了,就告诉我:我限你三天之内必须上这两家,把他那二千,他那二千,你都得给我要回来。我说你讲不讲理?那二千是你通知弟弟来找我拿去的,现在你又逼著我去要,那麼困难,我开不了这个口,我不去要,愿意要你要去。真不行,真跟我闹了。给我气的,我就去找我姑娘去了。
我就把这个经过说了,我说你爸就这麼不讲理。我姑娘说,我回去说。我姑娘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她爸说:爸,你讲不讲理?她爸说,我怎麼不讲理?你说我这两个叔叔他们从咱家拿的钱,是谁的钱?是我妈的钱,你就有四百,我跟你说,你有四百填进去了。我这个叔叔这个钱是你告诉他上我妈这来求的,都是你家的亲戚。你看,一个是我姑婆家的儿子,一个是我三叔公家的儿子,这不都是我老伴他们家的亲戚吗!我姑娘说,如果是我妈家的亲戚,要是这样,你还能作到什麼程度?你家的亲戚,我妈这麼处理,你还作我妈、闹我妈,逼著我妈去要钱,你怎麼想的?我说:是不行,明天我就去给他要去。我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不是想去要钱,因为我知道我两弟弟困难,我能去要去吗?我就想,你不让我要钱吗?我就出去,我起张票,我上这几家农村我转一圈我串个门,我散散心。回来以后我找个地方,我借四千块钱,然后我通通的都还给你,我钱要回来了,这个事就了了嘛。结果让我姑娘这麼一说,他泄气了,他也觉得自己理由不充足,也不坚持让我第二天就去要钱了。这个事就解决了。
就这个事解决了以后,感动了他,真是感动了他。我姐姐有病,因为我就一个姐姐,我姐有病,我姐是骨癌,那个腿肿的就是肿多粗?就二尺二的裤腿穿不进去。骨癌是特别疼的。因为我姐和我从小是一起长大,我姐特别关心我,她比我大四岁。妈妈去世以后,我姐就像妈妈一样对待我,可惯著她这小老妹了。就是当我有病的时候,我姐痛苦到什麼程度?到处去给我找人看病,不管神啊仙啊,那都不顾了,她知道我反对这个,我不赞成她这麼整。她不敢跟我打招呼,她自己拿我照片去找人去给我看去。真是哭到来哭到去的,就寻思我就这麼一个妹妹,可不能让我妹妹死,就这个。姐妹亲情真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我姐有病以后,我能不心疼她吗?我就把我姐接到我家来,我想我照顾她方便。我姐在我家住。
我老伴对我姐非常好,真是的。他跟我说,咱们俩现在就这麼一个大姐。你看,他是独生子,我这面就这麼一个姐,不是我俩就这一个姐吗。他说咱俩一定要好好善待大姐,让大姐减少痛苦。就这样的,说实在的,我真是挺感动。我老伴侍侯我姐,能跟我姐唠嗑。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后来这不是老叨咕《弟子规》吗?他听住了。他倒不是从头至尾学这个《弟子规》,人家这一点做得好,就是听一点,人家就能落实。他跟我说,《弟子规》怎麼说的,他说现在咱们的双方父母都不在了,就剩咱们一个大姐、一个大姐夫了,他俩就是咱们长辈,就代替咱们父母,咱俩得孝敬大姐和大姐夫。他提议去,不管是大姐来也好,还是上大姐那也好,得给大姐和大姐夫磕头。我就以为他说说而已,我真没想他真做。
有一次,我和我老伴上我姐那,进屋他就让我姐和我姐夫并排坐到这,我姐和我姐夫都挺纳闷的,干啥呀?他说我给你们磕头。我姐和我姐夫说,磕什麼头?他说你们两位就是我们俩的长辈,就代替我们的父母,过去父母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磕头,孝敬父母;现在父母不在了,我们就得给大姐磕头,给大姐夫磕头。跪地下就给我姐磕了三个头,嘴里还念念有词,还叨咕著,感谢大姐如何如何;磕完了,给我姐夫磕了三个头。你可知道,我姐夫那可是个倔老头,这三个头给我姐夫磕的,那眼泪哗哗的往下流。你说感人不感人?这个娇生惯养,这个性格,我姐夫是个倔老头,他们俩就能达到这种程度。这个倔老头给这个倔老头磕了三个头,结果把这个倔老头磕的双泪流。那个场面我觉得特别感人,就在这一点上,我不如我老伴,我做不到,我都没想到我要给我姐磕头,给我姐夫磕头。他想到了,他去身体力行,他去做去了。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我老伴太可爱了,我看他哪都好,都顺眼。
过去我看他不顺眼的时候,比如说做好饭了,我一样一样往上端,他就搁那坐著看电视,不带帮我端,拿一双筷子,端个碗的,都得我一个一个的往上端。现在我跟我老伴说,我说老伴你这习性是不是也得改改,我倒不是为了我轻松。他说:老伴,你别怨我,我就是从小这个独生子把我惯的,我从来不知道关爱别人,只知道让别人关爱我。他九岁了,吃饭他妈还嚼著餵,你说惯到啥程度!农村外面卖鱼的,他就跑回家告诉他妈:外面来卖鱼的了,拿鸡蛋去换几条鱼。换几条鱼,做好了,就著小米饭,他妈得搁嘴嚼了,再吐到他嘴里去。那都九岁了,还能惯到这种程度。我结婚以后,就是比如说老爷子、老太太,他、我,我们四个人,那是炕桌,坐炕桌上吃饭。饭盆就在我俩中间放著,他吃完饭要盛饭,他得把饭碗放到我这,我来盛,我盛完了再给他放过去,就是这样。按《弟子规》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但那时候不懂。后来有的佛友在我家说:姐夫,你这样不行,你看怎麼啥都让我大姐做?他说,那个时候如果你大姐不做,肯定是我妈做。老太太做,这是肯定的。
我结婚以后,我老伴上夜班的时候,他不下夜班,不上炕睡觉,我婆婆不躺下睡觉的,就那样事的。大烟袋一袋一袋抽,你听抽一袋,梆梆梆,磕灰,再按上一袋,抽完再梆梆梆。非得到她儿子下班了,收拾完了,上炕了,睡觉了,老太太那边才能睡觉,就是都把儿子惯成这种程度。她儿子和他妈有个暗号,我们这都一趟房一趟房一趟房的,下班从那趟房那房头转过来。什麼暗号?饭盒,饭盒里面不是有勺子吗?老妈一到快下班的时候,她儿子快下班了,就站门口望上了,迎上了。儿子那边回来,一到房头,哗啦哗啦就摇这饭盒,就向他妈报告:我回来了。这就是暗号似的,都这样。有一次,我老伴,半夜了,不是,白班,半夜了还没回来。老太太就著急了,说:小云,你就快去找找他。我说那工厂我也没有通行证,我进不去。你想想办法,快点去找找邻居谁谁谁,他们俩一个单位。我就去找那位大哥,半夜敲人家门,我说:大哥,我家明华没回来,他白班,他怎麼现在还没回来,我家老太太著急了,您去给看看呗。我这大哥起来就上单位去给看去了。你说我老伴干啥?跟人家下象棋!就是白班下班就跟人家下象棋,忘了时间了。人家夜班都要下班了,他这下棋还没下完。为什麼?要下三盘象棋,不是说他三盘都得赢,都差不多。你要是假如你第一盘,你要把他赢了,你别想回家,那你就得跟我下,我非得把你战胜了不可,就这样事的。后来我那大哥去说:明华,几点了,你还不回家?几点了?问人家。人家说:半夜几点几点。是吗?这麼快吗?说你家都找你都找翻天了,你快点回家。就这麼我大哥把他领回来的,就能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父母关爱子女的那颗心,子女,我说你可能不能百分之百的理解透。现在我们,我过去曾经是我爸爸妈妈的女儿,过去我也是我公公婆婆的儿媳妇,现在我是我儿女的妈妈,是我丈夫的妻子。我就觉得一个女人这一生,很不容易,很不简单,很伟大!为什麼?这个家我们也在支撑著,但是千万不要抱怨。我们应该尽职尽责的把我们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好,尤其是要把妻子的角色扮演好。你夫妻俩和谐了,你这个家庭就百分之八十以上就和谐了。你再继续努力,你整个家庭就和谐了。细胞和谐了,社会能不和谐吗?所以,你别小瞧你这一个家庭。我劝在座的各位,或是能看到这个直播的各位同修,切记,不可以离婚!离婚将来要去的地方相当苦。你那样想,一个家庭,现在往往都是一个孩子,我自己身边的,我看到的,凡是离异,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的心灵是扭曲的,他的成长过程和正常的孩子不一样。
我两个外甥女,这个外甥女的孩子,和那个外甥女的孩子不一样。同样是我的外甥女,这两个孩子到我那去,这个双亲家庭的孩子就自由自在,想跟我说啥就说啥,姨姥长姨姥短的。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就非常怯懦,好像什麼事都不敢靠前,就觉得他和这个,那就是哥哥,这个是弟弟,这个弟弟就觉得我不能像哥哥那样。这个哥哥在我面前就非常自在。实际你说,两个外甥女都是我亲外甥女,她俩是亲姐俩,这两个孩子我能哪个先哪个后?我都非常疼爱他们。但是这个孩子就明显不行,这个孩子原来在上小学的时候是优等生,是班干。后来到中学,逐渐的就往下滑。现在基本上可以说,社会上那些东西,沾染了好多好多。我曾经跟他唠过,我问他为什麼这样?他说:姨姥,您不知道,我小学的时候有多少人欺负我,他们欺负我的时候,在打我、骂我、踢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你没爹。他说我当时就想,我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报复。你看从小就扎下这个报复的种子,现在就是既恨自己的父亲,又恨自己的母亲。所以夫妻离异,受伤害最深、最痛苦的是孩子。那天傅冲讲的那个,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非常切合实际,非常有道理,那是她自己的切身体会。
所以咱们为人父为人母不要自私,不要为了自己的快乐,把孩子置於痛苦之中,他的整个的一生几乎就葬送了。他真是一种心灵的扭曲,他看问题和一些人完全不一样,为什麼?他就比较偏激,他就觉得对我不公平。尽管他的父亲也爱他,他的母亲也爱他,他不单没有一点感恩的心,我就是恨你们,现在表现得非常非常明显。他念大学以后,就是给妈妈打电话就是要钱,口气非常生硬,你给我寄多少钱,往我卡上打钱!有时候甚至连妈都不叫的。你这面你要不给他打钱,那就闹。你看我外甥女她的生活条件不是太好的,本身她自己就下岗了,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很困难。人家这个我不管你有没有钱,反正我需要你就得给我邮。这面这个孩子,他就生活在双亲家庭里,得到了父母的疼爱,所以他就是比较正常成长的一个过程。
我在这里为什麼在今天我提出这麼个话题,因为今天这话题主要说家庭和谐,特别是要说夫妻和谐。你知道,你夫妻和谐了,你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你不要单单看你夫妻之间,或者你对你的孩子,你对整个社会都是功臣,你一个家庭和谐了,这孩子不出去闹事。单亲家庭的孩子有多少泡网吧?我说那个网吧是怎麼回事,我也没去看过,我也不懂。但是我就知道网吧太害人了,把多少孩子都网进去,出不来了。我记得有一次电视里演的,一个优等生的孩子,十四五岁,班干部,从他家楼梯上到楼的最顶层,跳下去。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三年前电视里演的。为什麼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最后能从楼顶上跳下去?后来说了,就是因为上网吧上的,迷恋於网吧,他把那当做一种真实的生活。一旦他觉得和自己的距离比较遥远了,实现不了,他就采取了这种自杀。现在还有的孩子,叫自残,我原来不知道,我曾经看见我认识的一个男孩,他这手上就这个地方,一道一道的痕疤,像楼台阶似的。后来我问他怎麼回事,他告诉我,他说:刘姨,这叫自残,我自己拉的。我说干嘛?发泄!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平衡,内心的不满,内心的痛苦。所以咱们父母一定要从正面关心、关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要娇惯,娇惯是害他们。
今天这两个小时,我就跟大家说关於家庭方面的问题。晚上还有两个小时,晚上这两个小时是我来香港的最后一次跟大家交流了,这个我没犯错。那天我是犯错了,没经过师父允许,我就说这是最后一次。我昨天已经道歉了,师父会原谅我的无知和幼稚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