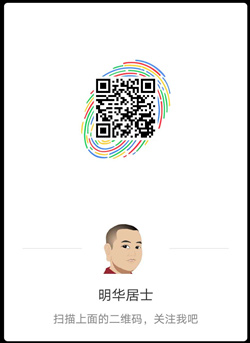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手机上长按二维码,进入明华学佛微博,点关注
Shou Ji Xue Fo Wang
禅不是哲学,而是……
阿部正雄著 王雷泉译
[按:本文是《禅与西方思想》第一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作者以西方人所熟悉的思辨方式,剖析了东方禅的思维特点。禅并非建立在不思量的基础上,所以不能把禅误解为反理性主义;禅也不是建立在思量的基础上,这样禅就会丧失其真正的内证基础。作者认为禅建立在非思量的基础上,超越了思量和非思量,并根据情况的需要通过思量或不思量而自在无碍地表现禅的自身。如果禅要走出禅院,有效地对治当代世界的苦痛问题,那么禅必须充分地运用这种非思量的哲学。]
人们很难深入精微地了解宗教,禅宗亦不例外。在某种意义上,禅宗可说是一种最难以为人理解的宗教,因为它没有一种可藉理智来探讨的系统表述的学说或神学体系。因此,在那些与禅宗所由发展的文化与宗教的传统迥异,但又热衷于禅的西方人中,出现了形形色色对禅的肤浅理解甚至误解,并不足奇。
1.1
在禅宗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诸如“柳绿花红”、“火热水凉”之类的寻常话。被公认为日本曹洞禅[1]创始人的道元[2]曾说道:“我是空手还乡,我在中国学到的不过是眼横鼻直而已。”这类话都是这样自明和寻常,倘若加以认真对待,反会令人糊涂。
不过,禅宗又有“桥流水不流”、“青山恒走、石女生儿”和“李公吃酒张公醉”这一类背谬的说法。的确,禅宗充满了诸如此类的说法,与上面引述的那些自明的话相比,这类说法完全是不合逻辑、不合理的。禅宗既用自明的表述,也用反逻辑的表述。禅因此常被都说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超越理智分析的东西”,从而被看做是一种反理智主义或肤浅直觉主义的形态,当禅悟被认为是一种电光石火般的直觉时,就更是如此。
再者,禅宗常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禅因而被误解为某种非道德性的、来自人的欲望或本能的东西,像动物一样不思善恶。最好的也不过是称禅为“东方神秘主义”。但是,若以这种指称来回答“禅是什么”的问题,那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显然,禅不是一种哲学。它超越了言语和理智,不像哲学那样是一种规定思想和行为的学问,也不是一种调节人与宇宙关系的原则或规律的理论体系。就禅的实现而言,修行才是绝对必需的。虽然如此,禅既不是反理智主义的,也不是一种肤浅的直觉主义,更不是对达到动物式自发性的一种鼓吹。更确切地说,禅蕴涵着一种深奥的哲学。虽然知解不能替代禅悟,但修行若无适当合理的知解形式,往往会误入歧途。知解无修行则弱,修行无解则盲。因此,我想尽可能来说明禅所蕴涵的哲学。
中国唐代禅师青原惟信的一段话,为我们进入禅宗哲学大门提供了一把钥匙。他说: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然后他问:“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3]这一问题是他全部说法中的关键。
这里所讲的第一阶段见解,强调“山是山,水是水”。这是禅师在习禅之前的见解。可是,当他习禅若干年后有所契会时,他领悟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这是第二阶段见解。但当他开悟时,他清晰地认识到“山只是山,水只是水。”这是第三阶段也是最后的见解。在第一阶段的见解中,惟信把山与水加以区分,“山不是水,而是山;水不是山,而是水”,以此将两者判然相分,从而肯定了山是山而水是水。这里既有区别性,又有肯定性。然而,当他达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第二阶段见解时,既没有区别性又没有肯定性,只具有否定性。最后,当他达到“山只是山,水只是水”这第三阶段也是最后的见解时,又有了区别性与肯定性。
1.2
在上述这段说法中,包含著许多重要的命题。在第一阶段见解中,惟信区分并肯定了山和水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同时,他把山客观化为山,把水客观化为水,由此达到对这两者的清晰了解。所以在第一阶段见解中,除区别性与肯定性外,还有着客观性。
如果有人问他:“是谁把山与水区别开来?”他当然会回答:“是我。我把山与水区别开来,我肯定山是山而水是水。”因此,在第一阶段,山之所以被理解为山,是因为山被他或我们客观化了所致,而不是根据山本身而理会为山的。山矗立于彼处,我们则站在这里从我们自己所站的地位眺望它们。“山是山”,仅仅是以我们的主观性观点来看客观化的山,并没有领会山的本身。它们是从外部,而不是从内部被人所领会。在这种见解中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二元性。在把山、水及一切构成我们世界的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时,我们也就把我们自己与他物区别开来了。于是我们说:“我是我而你是你:我不是你,而是我;你不是我,而是你。”在区别山水这一见解背后,存在着将自我与他物区别开来的这种见解。简言之,区分山、水和其他客观现象,与区分我和他物是紧密地相连结的。此中,“我”是这一区分的基础,“我”把自己置于万物的中心地位。
让我们把这种“我”称做自我(ego-self)。通过把自我与其他的自我区别开来,自我在与其他的自我相比较中了解了自己。自我因此与一切其他的自我处于对立的位置。所以,自我必然会自问:“我是谁?”这对自我是一个很自然的、必然会发生的问题,因为自我把包括本身在内的万物都客观化了。但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然会问:“是谁在问‘我是谁?’”自我也许会答:“是我在问‘我是谁’。”但在这个回答中,却出现了两个“我”:一个发问的“我”和一个被问的“我”。那么,这两个“我”究竟是同一的,还是相异的?它们必然是同一的,但又相互区别的,因为发问的“我”是问的主体,而被问的“我”则是问的客体。自我被一分为二。换言之,这里“我”正在问“我自己”,而在这一情况下,“我自己”就不是问的主体,而是被问的客体。这一“我自己”并非真正的主体性自我[4],因为它已经被客体化了,而一个客体化的自我绝不可能是一个活泼泼、真正的主体性自我。这个活泼泼的、行动着的主体性自我就是正在发问的“我”——即真我。
可是,我们怎样才能领会这个“我”呢?我们怎样才能认识我们的真我呢?为了做到这点,我们也许会发出这样的问题:“是谁在问:‘谁在问:我是谁’?”现在,另一个“我”做为一个新的主体出现了,并把全部情况转变为另一个问题的客体。也就是说,曾为前一问题主体的“我”,现在又被客体化了,转为一个新问题的客体。这意味著,做为真正主体性、做为真我的“我”,必然永远站在“后面”,永远逃脱我们的领会。因而,我们永远与我们的真我疏离,永远饱受焦虑的折磨,永远不可能得到安宁。
自我疏离和焦虑并非偶然发生于自我的,而是其结构所固有的。不管文化、阶级、性别、民族或所处是什么时代,做为人就是对他自己构成了问题。作为人就意味着是一个自我;做为自我就意味著与其自身及其世界分离;而与其自身及其世界分离,则意味着处于不断的焦虑之中。这就是人类的困境。这一从根本上割裂主体与客体的自我,永远摇荡在万丈深渊里,找不到立足之处。
当然也有人否认这种基本焦虑的存在。但即使是那些人也摆脱不了这种焦虑。虽然人们普遍逃避或抑制这种焦虑,但若作一严格的自我省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途径”是徒劳无益的。检查一下我们的生活,人难免陷入对死亡的恐惧,它把我们抛进无意义的陷坑;或是由于对我们行为不洁的谴责而时常引起的痛心的内疚。这种恐惧或内疚,把我们竭力逃避或抑制我们内心的基本焦虑而可能得到的一点安宁破坏殆尽。所以,除非我们首先克服自我并悟到我们的真我,人类生存所固有的基本焦虑和自我疏离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克服。
但是,真我却因我们反复询问自己而逐步后退。这一过程永无止境——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后退。然而,在不断被迫从事这一无穷尽的抓捕过程中,我们同时也被迫认识到:这个可能被抓捕到的东西,无非是一个客体化的、僵死的自我而已。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涉及对真我的认识时,南泉[5]才会说:“假如你朝向它,你就离开了它。”[6]临济也说:“假如你去觅它,它后退得更远;假如你不去觅它,它就在你眼前,它的神妙的声音在你耳中回荡。”[7]这种蕴涵在“客体化方法”中的无穷后退,表明这种方法的徒劳无益和必然失败。
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孜孜以求,做为真正主体性的真我,不可能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因此,面对着无穷的后退,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真我是得不到的。无论我们可以多少次反覆询问自己,我们的真我总是站在“后面”;它绝不会在我们“面前”出现。真我不是某种可得到的东西,而是不可得的。一旦这在存在上被我们以全力认识时,自我也就瓦解了。这就是说,我们在存在上认识到不可能得真我而终于陷入僵局时,突破这一僵局就导致自我的崩溃,从而认识到无我或无自我。而当自我消失时,“客体化”的世界也随之消失。这意味着处于第一阶段见解上的主—客二元性,现在已被消除。结果就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建立在客体化基础上的山水区分,现在已被克服。换言之,投射于山水之上的主观幕幛,现在被撕破了。同时,在无我的认识中,自他区分也被克服了。随着这种对无我的认识,我们到达第二个阶段。
1.3
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见解的否定,我们认识到,不存在任何分别、任何客体化作用、任何肯定性和任何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在这阶段必须说万物皆空。为了揭示最高实在,这种否定性认识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8]。但如果仅停留在这种否定性认识上,那将是虚无主义的。所以,虽在第二阶段克服了山水、自他的分别,但依然蕴涵着另一种形式的分别。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分别,即在第一阶段的分别和第二阶段的无分别之间的分别。做为只是对分别之否定的“无分别”,依然陷入一种差别中,因为它与“分别”对立并反对分别。为了认识真正的、无差别同一性的最高实在,我们必须克服隐藏于“无分别”背后的更高层次上的分别性。甚至连“无分别”、“非客体化”,我们也必须加以否定,并超越第二阶段。否定性的观念也必须被否定。空必须空掉自身。这样我们就到达了第三阶段。
在这方面必须注意的是,第二阶段具有双重的涵义:
一、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所含问题的一种终结或解决。它只有通过如下途径才能达到:认识到自我在“客体化方法”中的无穷后退,并认识到真我的不可得性。因为这种对后退之无穷和真我之不可得的认识,必定是一种总体上的和存在上的认识,而不是那种片面的和概念化的认识,自我的焦虑和不安于是在这一意义上被克服。当这种探索的徒劳无益,而又必要将自我逼迫到一种无法维持“客体化方法”的极限状态时,通过对真我的不可得性的痛苦揭露,自我的主—客结构就崩溃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指出,为使第一阶段的自我现实化为第二阶段的无我,自我——当它仍正在或从事于企图解决“客体化方法”的困境时——仅仅感觉到或在理智上直观到真我之不可得,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这样,那么自我将处于更为绝望的困境中,因为它唯一的目标和希望向来是获得自己的真我。这种绝望正是自我仍未摆脱执著的一个标志。相反,即便为了克服这种极端的绝望,自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彻底认识到后退之无穷和真我之不可得,进一步推进自己,进入僵局,并且瓦解。认识到真我实际上不可得,即认识到真我就是空和非存在。这意味着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途径,更确切地说,这里存在着间断,只有通过飞跃才得以克服,在这一飞跃中,自我被迅速而彻底地打破。实现无我,需要从自我和内在于自我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因此,对“真我不可得”的真正认识,不是绝望的根源,而是对焦躁不安的解脱,因为在这种认识中,真我的不可得已无关宏旨了。自我及与其有关的世界就在无执着中得到领会。这就是为什么惟信在第二阶段要说“我悟入禅的真理。”[9] 在这种洞察中,洋溢着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二、然而,如前所述,即使在第二阶段的“无分别”中,仍蕴涵着一种隐蔽的分别形式——即“分别”与“无分别”、自我与无我间的分别——这样仍未完全摆脱差别性。因此人们仍易于把无我客体化,把无我执着为有别于自我的一种东西。在第二阶段所认识到的“无执着”中,仍潜存着一种隐蔽的,消极性的执着形式。这样一种对无我的执着,导致一种对自我和世界漠不关心和虚无主义的观点。对人们的生活和活动没有积极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还不能说第二阶段已摆脱了隐蔽的焦虑形式。甚至“安宁”也没有完全摆脱隐蔽的不安宁。因此必须克服第二阶段,并突破到第三阶段。为了悟到真我,就是连无我和它的隐蔽的执着和焦虑也必须加以否定。这种否定也必须是总体上的和存在上的,而不是片面的和概念化的。此外,由于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没有连续性的途径,为了达到这个最后阶段,必须有一个飞跃。
当我们达到第三阶段时,就有一种全新的分别形式。这是一种通过否定“无分别”而被认识到的“分别”。在此我们可以说:“山只是山,水只是水。”山水在其总体性和个体性上揭示了自身,而不再是从我们主观性立场上看到的客体。
在第二阶段上有否定,可是在第三阶段上必须再有一个否定。从逻辑上说,这样我们有了否定之否定。但什么是否定之否定?做为完全的否定之否定,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肯定。不过它不仅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肯定,而更确切地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肯定。它是一种真正的和绝对的肯定。现在,在第三也就是最后阶段中,山和水按它们的本来面目被真正地肯定为山和水。空空成了不空,也即真正的圆满。在这里,一切形式的焦虑和执着——公开的和隐蔽的、清晰的和内涵的——都完全被克服。
随着对山和水这种真正的肯定,我们获得对真我的认识。只有全部否定无我,才能认识到真我,而全部否定无我也就是全部否定自我。再则,完全否定的完全否定,对获得做为真正肯定的真我是必需的。人们不仅可以将肯定性的东西客体化,同样可以将否定性的东西客体化。人们可以把“无我”如同“自我”一样予以概念化。为达到最高实在并悟到真我,克服一切可能的客体化作用和概念化作用,需对“客体化方法”进行双重否定。为澄清对真我的认识,下面一段论述必须予以注意:
“客体化方法”中固有的无穷后退,结果使我们终于认识到真我不可得;这里产生了从自我到无我的飞跃。虽然对无我的认识,一种对真我不可得的认识,是必需的和重要的,但它仍是否定性的和虚无主义的,引起无我与自我对立的一种二元论的观点。只有当无我在存在上被克服,才能悟到真我。从认识(A)——真我不可得到认识(B) ——不可得本身就是真我的这个运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1.4
我们不妨以一堵墙的比喻来解释这一观点。持“真我可得”之见的自我(第一阶段),建立在类似于一堵不透明墙的意识模式基础上,阻碍了自我的视野,从而看不见实在。对比之下,持“真我不可得”之见(A)的无我(第二阶段),建立在类似一堵透明墙的意识模式基础上,通过它可以毫无阻碍地见到实在。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必须排除这不透明墙阻挡一切色与光的性质。因而第二阶段的墙是完全透明的。由于第一阶段导致甚至不可能瞥见一下实在的、对色与光的阻挡性质已随着突破到第二阶段而完全消除,通过这透明的墙,实在现在已能被无我清晰地看到。
因此,随着对无我的认识,“我”容易把墙的透明性与墙的消失混同起来,因为墙虽然只是透明而已,看起来好像不复存在。这样,这个“正在见到”实在的“我”,就错以为自己等同于实在,在这个“我”与实在之间不复存在任何差距。无疑,通过透明的墙看到实在,与全然不能瞥见到实在,这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异。不过,只要墙依然存在,这个“我”就依然与实在分离。所以,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即使客体化方法已从肯定的转变为否定的,就像从不透明墙转变为透明墙一样,自我的基本存在方式及其永远存在的“客体化方法”还是没有得到改变。
但是,自我的基本任务并非是排除不透明墙的阻挡色与光的性质,籍以使墙透明而见到实在;毋宁说,为了彻底克服“见者”与“被见者”、“我”与“实在”之间的差别,它要突破墙的本身,不管这墙透明与否。突破墙本身,也就是突破到认识(B),那时人们认识到不可得本身就是真我,这就是第三阶段。
突破这堵墙,自我(为不透明墙所阻之自我)与无我(为透明墙所阻之自我)都被克服,最高实在的无分别的同一性——同时也是最清晰的分别——就被揭开了。在这里,“不可得”或“空”不再被看做“他在”(over there)的东西(即使通过透明的墙),而是直接被认识为真我的基础。这不仅是把肯定性的客体化模式转变为否定性的,而是一种更加彻底而根本的对自我基本存在方式的转变。
如同用墙作譬喻一样,我们还可以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说明从认识 (A)(真我不可得)到认识 (B)(不可得本身就是真我)的转变。如把这两个认识看做逻辑“命题”,认识 (A) 和认识 (B) 都可以看做由一个主词和一个宾词所组成,而由系词“是”加以连结。但是,在认识 (A) 中所表述的命题的主词和宾词,在认识 (B) 中完全被倒了过来。在关于“真我”的命题所表达的认识 (A) 中,“不可得”被视为“真我”的宾词属性。由于宾词(即“不可得”)是否定性的,该命题所表达的认识 (A) 也是否定性的。这一命题可以重新表述为:“做为真我的我是空的,或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在关于‘不可得’这一命题所表达的认识 (B) 中,“真我”被视为“不可得”宾词属性。虽然在这一命题中,某种否定性的东西(即“不可得”)被当作主词,由于宾词是肯定性的(即“真我”),因此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价值论上看,该命题所表述的认识 (B) 是肯定性的。这一命题可以重新表述为:“空本身就是做为真我的‘我’。”
对认识 (A) 和认识 (B) 的这种逻辑分析,也许有助于理解从认识(A)飞跃到认识 (B) 的存在上的意义。
在认识 (A),亦即第二阶段的认识中,真我被认做某种否定性的东西(“不可得”或“空”),从而在此意义上摆脱了客体化和概念化的作用,因为真我在这里被理解为不存在的。不过在这一理解中,真我仍有一些概念化和客体化,因为即使自我垮掉而认识到无我,真我仍做为“不可得”的或“空”的某物而处于外在的地位,从而尚未完全地摆脱实体性(somethingness)。真我依然客观地被想像(尽管其否定性意味多于肯定性),它因在此中充当“真我不可得”这一否定性命题中的主词而被客体化或实体化了。同时,“不可得”在认识 (A) 中亦从外部被客观地想像,从而也不是在总体上和存在上被认识为真正的“不可得”。它只是被理解为真我的属性。
简言之,即使以一个否定性的宾词(“不可得”)做真我的属性,只要真我以一个宾词属性来领会,那就不得不说它已被概念化了。因此在认识(A)与做为真我的“我”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所知与能知仍被二元化地割裂了。
然而,当我们进入认识 (B),即认识到不可得本身就是真我时,无论是“真我”还是“不可得”,都丝毫不被客观地表达了,因为在这一认识中,“不可得”本身被认为“我”——被认为真我。换言之,在认识 (B) 中,不是“我即空”,而更确切地说是“空即我”。通过克服“我即空”这种否定性的观念,空在主体性上和存在上被认为真我的“我”。因此在认识 (B) 和“我”之间不再有任何鸿沟。所知即是能知,而能知即是所知。在关于“不可得”的命题所表述的认识 (B) 中,真我被理解为一个宾词属性。这里,“不可得”不再被理解为真我的属性,因此它不再是不可得的某物,而就是“不可得”本身;它被认识为积极的主体。另一方面,作为宾词的真我完全摆脱了实体化和客体化的作用,按其本来面目在存在上得到认识,因为它不再被理解它本身的某种属性,并从实体性中摆脱出来。它本身做为真我而真正非客体化地被悟到。
这样,在认识到不可得本身就是真我的认识(B)中,一切可能的概念化和客体化作用不管是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都被彻底克服。在第二阶段仍带有某些概念化的空,现在被彻底空掉;永远空掉自身之空的纯粹能动性,被认识为真我。自我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有了彻底而根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并不仅像在第一阶段对自我的肯定性(虽然是成问题的)理解,变成第二阶段对自我的否定性理解。因为在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自我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尽管在第二阶段中这自我是在否定性意义上被理解为不可得或空的。更确切地说,在这一转变中必须将“不可得”或“空”理解为真正的中心,以取代将自我做为中心。真我以“不可得”或“空”而被悟到——空充盈整个宇宙,以此做为它的基础和根源。
随着真我被悟到,最终的实在于是被全部揭示。这里,自我疏离与焦虑被根本克服,因为“不可得”不再被认为某种否定性的或虚无性的东西,而是被肯定地认为“真我”。在认识 (B) 中,能知和所知并非两件事,而是一件事。在临济的意思中,“父母未生你前的本来面目”和“无位真人”,无非就是这个“不可得”的真我。
当后来成为禅宗二祖慧可的神光问菩提达摩[10]如何安心时,菩提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
神光回答(可能过了一些时候):“觅心了不可得。”
然后菩提达摩说:“与汝安心竟!”[11]
在这一段著名的故事中,假设神光这些话的意思是认识 (A) 的话,那么他的觅心了不可得的回答,菩提达摩是不会接受的。只是因为神光表达了认识 (B),主张不可得本身就是他的心,所以菩提达摩才予以印可。
1.5
现在,我们回到惟信在他说法结束时提出的问题上,即:“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从表面上看,第三阶段类似于第一阶段,因为两者都表达了山与水的确定性和差异性。但实际上它们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在第二阶段的否定之前,第一阶段仅提出一种不加批判的肯定,而第三阶段则道出一种真正的肯定,它是第二阶段中否定的必然结果,又超越了这一否定。第二阶段显然迥异于第一和第三阶段。因而每一阶段都不同于其他两个阶段。但是,它们只是不同于其他阶段吗?这必须加以仔细考察。
第一阶段不可能包括后两个阶段,第二阶段也不可能包括第三阶段。另一方面,第三即最后一个阶段则包括了前两个阶段。这意味着第二阶段不可能依据第一阶段的基础而了解,而第三阶段也不能依据前两个阶段的基础而了解。这里不存在连续性,也不存在由低向高的桥梁。如前所述,在每一阶段之间,有的是一种完全不连续性或间断性。为达到更高的阶段,必须有一个大飞跃。这里克服不连续性,就表示全面的否定或空。否定或空掉第一阶段到达第二阶段。否定或空掉第二阶段到达第三阶段。简言之,只有把全面的否定全面否定掉才能实现第三阶段,也即对前两个阶段的绝对否定或双重否定。如前所述,绝对否定就是一种绝对肯定。它们是动态的同一。因此,第三阶段并不是从低到高渐次达到一种静态的终极,而是一种动态的整体,它包括绝对否定和绝对肯定。在这动态的整体中,你和我融合为—,它无所不包。
因此,我们可以回答惟信关于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的问题:“它们是别,同时又是同;它们是同,同时又是别。”
这里面,有三点必须注意:
(1) 虽然以上对三个阶段间关系的解释是相当逻辑性的,但我们却不能把它们仅看做逻辑上的问题,而要把它们当作一个紧迫的存在性问题来看待。作为克服高低级阶段间“不连续性”手段的否定,不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否定,而是在最终的存在意义上的一种“克制”、“自我否定”或“舍弃”。
换言之,通过对第一阶段(自我)的否定而在第二阶段(无我)实现的,必须是一种在总体上、存在上的对自我的自我否定。它必须不是自我对某些外部事物的外在否定,甚至也不是对作为客体之自我的自我舍弃,而更确切说是自我本身的否定和崩溃——包括任何通过认识到“客体化方法”中的无穷后退及真我不可得而成为那个自我的所谓主体舍弃者。这就必须使自我死去。同样,通过否定第二阶段(无我)而实现第三阶段(真我)的否定,也必须是对无我的一种总体上、存在上的自我否定,在这一否定中,通过完全认识其自身的隐藏焦虑和内含的执着,无我就被冲破。因此,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绝对否定”,必须在其最根本和存在的意义上被理解,也就是,只有通过对自我的总体的自我否定才实现的对无我的总体的自我否定。这一彻底的双重否定,就是完全回到“自我”的最根本基础——一种比自我的“原始”状态更为原始的基础。通过这种根本性的回复,原始的真我就被悟到。因此,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绝对否定”,同时也是“绝对肯定”。在这意义上的“绝对否定”是指打破自我与无我、生与死的“大死”。若无这样一个“大死”,作为复活的“大活”就不可能发生。
(2) 在“山只是山,水只是水”的第三阶段见解中,看来似乎是一种对山水的纯客观认识。但这并非自我在客观地谈论山水。恰恰相反,是真我在谈论自己。进一步说,这并不意味着真我是把山水当作它自我的象征来谈论,而是真我把山水当作它自身的实在来谈论。在“山只是山,水只是水”这一陈述中,真我是同时谈论自己和谈论作为自己的实在的山水。这就是因为在第三阶段中,完全克服了主—客二元对立;主体本身就是客体,客体本身就是主体。
要克服主——客二元对立,只有通过第二阶段“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认识才有可能,与这一认识密切相关的,是“我不是我,你不是你”这一认识。因此,禅宗与自然神秘主义或泛神论不论怎么相似,两者不应该混为一谈。因为后者缺乏一种对主客体否定的清晰认识。
(3) 虽然我们在分析惟信的说法时使用了“阶段”一词,但这词并不恰当,即使用做理解他说法的真正涵义的辅助,也会产生误解。因为如前所述,“第三个阶段”并不是一种从低级阶段渐次抵达的静态终结,而是一个包容肯定性的和否定性的两个低级阶段的动态整体。它不只是第三或最后阶段而已。它是个赖以克服过程概念,甚至“阶段”概念,以及它们所意味的时间顺序的立场。“山只是山,水只是水”,是以完全非概念化的方式,在绝对现在中被认识的,它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而又包容了过去、现在、未来。正是在这绝对现在中,包括所有三个阶段的动态整体被认识到。根据这一观点,建立在“阶段”概念基础上的方法是虚幻的,与“阶段”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时间性见解也是虚幻的。
在禅宗中,山水(以及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完全真实,是通过对蕴含于“阶段”概念中的时间顺序的双重否定而实现的。否定蕴含于“第二阶段”中的非时间性及蕴含于“第一阶段”中的时间性,绝对现在就被完全揭示。
因此,在绝对现在对万物本来面目的认识,就不只是在时间中的客观方法的最后阶段或终结,而是超越了时间,是客观方法赖以确立的根源或原始基础;从这基础出发,时间顺序才能合理地开始。在时间中的“三个阶段”因其缺乏绝对现在的基础而虚幻不实,它们只有在这一认识中才能复原为一种真实的东西。绝对现在也是万事万物赖以认识它们本来面目的根源或基础,在这基础上,万事万物既没有失去它们的个性,也没有相互对抗和妨碍。
这样,在惟信所获的禅悟中,一方面,山本是真山,水本是真水,也就是说世界万物皆如其本然。但在另一方面,每一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都任运无碍,万物都是平等的,相互交替和相互融合的。从而我们可以说:“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就在绝对否定也即绝对肯定这样一种悟中,禅宗才说:“桥流水不流”,“李公吃酒张公醉”。也正是这样一种悟中,禅宗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这并不是一种可见诸“第一阶段”中的本能的、动物般的活动,而是吃与眠依赖于对深不可测的无的认识。当你饥时,除饥之外别无他物。你就是饥而已。当你吃时,在吃之外也别无他物,吃就是那时的绝对行动。当你眠时,眠之外也别无他物,无梦无魇,只是眠而已;眠是那时的彻底实现。在这种悟中我们还可以说:“我不是我,所以我是你;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我真是我。你不是你,所以你是我;正是因为这一理由,你真是你。”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妨碍,可是每个人又有完全的个性。所以可能这样,是因为真我就是无我。由于我们之后别无他物,每个人都是他或她,可是每一个人又都与其他任何人圆融无碍。因此,“李公吃酒张公醉”,“桥流水不流”,这并不是暧昧不明的话,而是禅的圆融无碍的一种表述,正如在“柳绿花红”、“眼横鼻直”中所表述的那样,禅的圆融无碍又与每一个人、动物、植物和事物的独立性和个性不可分离地连结起来。
1.6
这就是在禅宗中所认识到的哲学。有人也许会觉得这与黑格尔哲学并无多大差异。的确,在黑格尔哲学与禅宗所蕴涵的哲学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处,尤其就否定之否定就是真正的和绝对的肯定这一点而言。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强调用否定这一重要概念来解释辩证法时,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而辩证地把握一切事物。黑格尔的辩证法过程,被理解为作为最终实在的绝对精神(absoluter Geist)的自我发展。例如,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的意义被理解为绝对精神在时间中通过一系列诸如凯撒和拿破仑这样的世界历史人物的经历而得实现。对黑格尔来说,由于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的,人类的现实历史被理解为是在绝对精神的逐渐展开中人的自由的发展。虽然黑格尔主张一切历史事件都是通过个人的意志和私欲而发生的,但他将其归诸“理性的狡计”(List der Vernunft),是它把这意志和私欲作为工具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对此甚至个别的历史行动者也不是清楚地认识到的。虽然他对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解释是相当辩证的,但是,“理性的狡计”这一概念指出,个人并不是完全地作为个人来把握的。为使个人真正地把自己当作个人来把握,他必须与绝对辩证矛盾地同一。因为,假如个人与绝对被认为即使只有些微的分离,那么前者的个性在后者的绝对性之前就不能完全保持。反之,假如绝对与个人有些分离,那么它的绝对性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如所公认,个人与绝对在某种意义上是根本不同的。然而,如果个人要成为真正的个人,他就必须与绝对(辩证矛盾地)同一;同时保持他作为个人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如果绝对要成为真正的绝对,它就必须与个人(又是辩证矛盾地)同一;同时保持它的绝对特性。这种个人与绝对的辩证矛盾的同一性不可能从客观上得到充分理解,只有从非客观性和存在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
只有当绝对在非实体性意义上被把握——只有在不存在什么隐于个人背后或超于个人之上的“绝对”这种实体性东西时,个人才有可能与绝对辩证矛盾地同一。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个人不能被充分地把握为个人,因为对黑格尔来说,绝对并非是绝对无,而是绝对精神,归根究底是某种实体性东西。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只是实体性的东西,也许是不确切的,因为它是一个极其辩证的概念,它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它就不能说是实体性的。可是,根据禅对绝对无或空的认识,黑格尔绝对精神概念的实体性质就昭然若揭了。进而考虑到他那“理性的狡计”这一概念,人们就不得不认为在个人背后有着某种东西,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那某种东西——即绝对精神——的摆布。
另一方面,绝对在禅宗中被把握为无,亦即绝对无,这完全是非实体性的,因而个人得以与绝对辩证矛盾地同一,从而个人也就完全被认识为个人。不存在任何隐于个人背后或超越个人之上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摆布或控制个人——不管它是绝对精神还是上帝。在禅对绝对无的认识中,个人绝不受制于任何东西。绝不受制于任何东西,意味着个人在个体性上完全是自决的。它是完全自主的而无需任何超在的决定因素。这一事实对任何个人都是同样成立的。因此,通过并超越“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第二阶段)这一否定性的认识,就有了对“山只是山,水只是水”(每一事物的绝对个体性)和“山是水,水是山”(每一事物都可相互交融)这两者的肯定认识。更准确地说,通过第二阶段的否定性认识,在禅悟中对每一事物的绝对个体性和相互交融性都有了肯定性的认识。个体性和交融性被认为不过是同一的动态实在的两个方面。由于动态实在是一个动态整体,它是完全不可被客体化并且是非实体化的。
虽然极端辩证,但与禅的绝对无概念相比,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并未完全摆脱“实体性”。结果,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否定之否定并未被认识为完全的自我否定之自我否定,而是在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框架内被认识,不管自我发展的过程是辩证到什么程度。但在禅宗中不存在这种框架。一切皆空。万物在广大无限中被认识。空就是实在。在这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性质——完全自我否定之自我否定——得以充分实现。“否定之否定”(真正的空),同时就是肯定之肯定(不思议存在的真正圆满)。以一种非概念化的、存在上的方式,真空与真圆满是辩证的统一。两者丝丝入扣,毫无间隔。正是这样一种实在,在绝对现在中被认识为一种动态的整体,在其中个人在空间上的存在和在时间中的无穷发展的关系被正确把握住了。
上述黑格尔与禅宗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对哲学与宗教的理解不无关系。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哲学代表绝对知识(absolutes Wissen),对此形态上尚未摆脱信仰(Glaube)上帝的表象作用(Vorstellung)的宗教,只能处于从属于哲学的地位了。哲学位于宗教之前,这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是按照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而被把握的。与之相反,建立在对绝对无的认识基础上的禅宗,在黑格尔思想的意义上,则既非哲学,亦非宗教。在禅宗中,宗教并非如黑格尔那样被认为是哲学的附庸;亦非如基督教那样被认为哲学从属于宗教。在表述为“山只是山,水只是水”的动态认识中,兼容并蓄了智慧与慈悲,哲学与对人类困境的宗教解答。这就是为什么禅既不是绝对知识也不是上帝拯救,而是自我觉悟。在禅的自我觉悟中,每一个体存在,不管是人、动物、植物还是物,都如“柳绿花红”所表述的,在其个体性上显示了自身;然而,又如“李公吃酒张公醉”所表述的,每一事物又都和谐地相互交融。这当然并非目的,却是一个我们的生命与活动必须完全建立在其上的基础。
1.7
禅宗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不曾动他‘广长舌’。”又说:“一落言诠,即失其旨。”禅宗没有须用语言或理论来解释的东西,也没有当作神圣教条来学习的东西。事实上,禅的核心就是“不可说”。因此,当一位僧人问“如何是佛法的大意”,临济立即答之以“喝!”但是,由于禅宗所关心的是真正的不可说,它不仅反对言说,也反对寂默。所以,德山[12]在其说法中,曾扬棒说:“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13] 首山[14] 有一日举竹篦问其弟子:“唤作竹篦即触,不唤作竹篦即背。唤作什么?”[15] 禅总是以单刀直入的方式,表达那超出臧否语默的“不可说的”实在,通过“道!道!”的命令逼迫我们陈述这个实在的理解。
但禅宗并非单以断绝一切弟子们所有的可能办法(语或默,臧或否))来指出这“不可说”;如前述德山与首山的例子。如临济的“喝”,虽是一种绝对的否定,它切断了提问者每一种所想像得到的回答;但它同时又是对“不可说”的极度肯定。对“不可说”的这种肯定,在禅宗里是极其重要的,它也是一种单刀直入的表达,就像下述对话中所表示的:
石巩[16]问西堂[17] :“汝还解捉得虚空么?”
堂曰:“捉得。”
师曰:“作么生捉?”
堂以手撮虚空。
师曰 :“汝不解捉。”
堂却问:“师兄作么生捉?”
师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声曰 :“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脱去。”
师曰:“直须恁么捉虚空始得。”[18]
这一切例子清楚地表明,禅宗的目标永远在于把握生命中活泼泼的实在,而这不是光凭理性分析就能完全把握住的。但正如前面所述,这绝不能被当作只是反理性主义。禅虽然超越了人的理性,但并没有排除理性。所谓一旦从理性或哲学上去理会和表达,禅的“认识”(悟)就衰退或消失的说法,必须说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根据的。真正的禅悟,即使它经过严密的理性分析和哲学思考,也绝不会被毁坏;相反,分析将有助于给自己阐明这种认识,并进而使人们能把这种认识的精微之处传达给他人,即使这要通过语言的中介。
下述四句偈可以表达禅宗的基本特征: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不过,“不立文字”,并非像甚至有些修禅者也误解的那样,仅仅表示排除语言或文字,不如说它表示必须不拘泥于语言文字。只要不拘泥于语言文字,人们即使在禅的领域里也能大量运用它们。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强调“不立文字”,禅宗却产生了丰富的禅宗文献和像道元那样思辨深刻的思想家。
禅宗说过:“未开悟者应参透实在的意义,已开悟者应将这实在用言语表达出来。”又曾说:“开悟是容易的,自由而不执着地讲出这个悟就难了。”禅是一把双刃剑,既斩去语言和思量,同时却又赋予它们以生命。禅虽然超越了人类的理性和哲学,却是它们的根本和源泉。
当药山[19]坐禅时,有一僧问道:“兀兀地思量甚么?”
师曰:“思量个不思量底。”
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
师曰:“非思量。”[20]
禅并非建立在思量或不思量的基础上,更确切地说,它建立在非思量的基础上,这超越了思量与不思量。当不思量被当做禅的基础时,反理性主义就会变得猖獗。当思量被当做禅的基础时,禅就会丧失其真正的基础,蜕化成单纯的概念和抽象的冗词赘语。然而,真正的禅把非思量当做它的最终基础,从而可以根据情况的需要,通过思量或不思量而自在无碍地表现禅的自身。临济喝,德山棒,南泉斩猫[21],俱胝竖指[22],这一切都包含着非思量的哲学。如果要禅不停留在禅院中,而是有效地对付使当代世界苦痛的许多问题,那么禅必须充分地运用这种非思量的哲学。禅并非一种反理性主义,也不是一种肤浅的直觉主义,更不是一种动物式的活动,而是包含一种最深奥的哲学,虽然禅本身并非哲学。
--------------------------------------------------------------------------------
[1] 曹洞禅,即佛教禅宗五家之一曹洞宗。开创人是我国唐代洞山良价(807-869)和其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僧道元入宋,在天童山从洞山第十三代弟子如净受法,向日本传入曹洞宗,以永平寺(在今福井县)为中心传教。——译者
[2] 道元(1200-1253),全称“希玄道元”,日本佛教曹洞宗创始人。——译者
[3] 《五灯会元》卷 17 。——译者
[4] 在日文中,主观的和主体的两词皆可译成英文主体性(subjective)一词。“主观的”相当于认识论意义——是在如何理解、思维或认知意义上使用的——英语中的反义词即“客观的”(objective)。“主体的”则更多地涉及在动力学上的、存在上的承担责任的自我,具有道德上、伦理上或宗教性质上的自决能力。这表明在存在上承担义务的立场,这一立场超越了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二分法。为表明这种区别,本书用主体性表达这层意思。
[5] 即唐代南岳系禅师普愿(748-834)。——译者
[6] 原文作“拟向即乖。”见《五灯会元》卷4(赵州从谂禅师)。——译者
[7] 原文作“著即转远,不求还在目前,灵音属耳”,见(古尊宿语录)卷4。——译者
[8] 无分别(第二阶段)的否定性认识,对于最高实在的揭示(第三阶段)是必要的,但这并非意味著,在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认识之间必须有一时间差(time gap)。在禅修中,“第二阶段”的无分别或无我的否定性认识,与“第三阶段”的真正分别或真我的肯定性认识,可以是同时发生的。大死一番才有大活,按严格意义上说,这无非表明是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同时发生的认识。可是,正如惟信在他的说法中所清楚表明的,他所经历的第一、第二、第三阶段是前后相继的。这样一种逐步深化的禅悟过程的明确记录,在文献中是罕见的,以至现代作者在分析惟信在禅修体验时,只能沿著这条逐步深化过程的线索。但是,这种分析并不排除在禅悟中第二、第三阶段的认识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实际上,正如笔者在本后半部分中所阐述的,在真正的禅悟中,第三即最后阶段包含了前两个阶段,甚至连“阶段”这一用语亦不甚恰当,因为禅悟是在存在上对最高实在的觉悟,它超越了否定性和肯定性,也超越了任何渐进的方法。
[9]原文为“有个入处。”——译者
[10] 菩提达摩(Bodhidharma,?-528),南印度僧人,被称为“西天”(印度)禅宗第二十八祖和“东土”(中国)禅宗始祖。——译者
[11] 见《五灯会元》卷1。——译者
[12] 德山,即唐代青原系禅师宣鉴(782-865)。——译者
[13] 《五灯会元》卷7。——译者
[14] 首山,即宋代临济宗禅师省念(926-992)。——译者
[15] 《五灯会元》卷11。——译者
[16] 石巩,即唐代禅师慧藏,为马祖道一(709-788)弟子。——译者
[17] 西堂,即智武禅师,与石巩慧藏同为马祖道一的弟子。——译者
[18] 《五灯会元》卷3。——译者
[19] 药山,即唐代青原系禅师惟俨(751-834)。——译者
[20] 《五灯会元》卷5。——译者
[21] 南泉(唐代南岳系禅师普愿)斩猫:“师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来失却火。师因东西两堂争猫儿,师遇之,白众曰:‘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众无对。师便斩之。”见《五灯会元》卷3。——译者
[22] 俱胝竖指,禅宗公案。唐婺州金华山俱胝和尚因天龙和尚竖一指得悟。自此凡有学者参问,唯举一指,无别提唱。见《五灯会元》卷4 。——译者
——阿部正雄著 王雷泉等译:《禅与西方思想》第一章,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